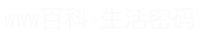回故乡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回故乡
我的舅父符年柏 , 海南文昌人 , 大学毕业后为国民党空军地勤服务 。 1948年随部队去台湾 , 成为空军一名会计师 。 这离家一走就是几十年音信全无 。 父亲死了 , 母亲瞎了 。 说来也怪 , 他的母亲整天念念有词:“我的儿子没有死 , 我的儿子没有死 , 他一定会回来看我的 , 一定会的!”我们都认为她想儿子想疯了 , 可是1988年8月奇迹出现了 , 我的舅父回来了 , 真的回来了!
在台湾的四十年 , 是思乡的四十年、渴望的四十年、等待的四十年 。 舅父几乎游遍了整个世界 , 却不能回到隔海相望的故乡 。 他挖空心思曾无数次想转道回家看看 , 都不能如愿 。 也许是身份特殊的缘故 , 当台湾当局打开亲情之门的时候 , 舅父早早就去申请 , 可是迟迟没有批下来 。 他动用了很多关系 , 打通了无数关节 , 总算批下来了 , 即将成行时 , 却得到噩耗 , 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不幸车祸身亡 。 是奔丧还是回家?我可怜的舅父 , 生怕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到故乡的怀抱 , 再也见不到故乡的亲人 , 于是强忍悲痛弃丧 , 踏上回故乡之路 。
回家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 与母亲抱头痛哭 , 与邻里遥忆当年 , 寻找后山捉迷藏的地洞 , 在门前的小河戏水 , 白发黑发 , 乡音乡俗 , 那情那景令人心酸动容 。 舅父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和良好的文学修养 , 几乎是出口成章 , 情浓意切 。 我的记事本上 , 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舅父当年近乎迸发般的内心倾诉――
“你知道吗?海峡的水为什么特别咸?因为那是千千万万人的眼泪 , 还有母亲的眼泪啊!
你知道吗?‘望夫石’、‘望妻岩’时时刻刻都有凄婉的歌声 。
你知道吗?有家不能归是怎样一种滋味?
我本不该早生华发 , 脸上也不该有那么多的沟沟壑壑 。 苦苦熬了几十年 , 思念了几十年 , 盼望了几十年啊!只有在梦中 , 我才是一只小鸟 , 飞回母亲的怀抱 。
多少月明之夜 , 纷乱的思绪搅得我泪如泉涌 。 恍惚中看见了母亲憔悴的面容 , 当我张开双臂扑上去的时候 , 却空荡荡的只有我辛酸的影子 。
我好像一个病危的人 , 我之所以还活着 , 是因为我坚信母亲在为我输血 。 我感到我的血是热的 。
我曾寄语给星星 , 可星星只对我眨眨眼;我曾把心思托付给白云 , 可白云默默无言;我曾对着茫茫的大海呼唤 , 可没有任何回声 。 难道天公也不理解这肝肠寸断?难道亲人就永远这样天各一方?
有人死了 , 又有人死了!可没有一个能安详地闭上眼睛 。 我隐约看见那失去光泽的瞳仁中定格了一个故土的幻影 。 他们的遗嘱都那样不约而同的写下一个重重的‘恨’字!这个‘恨’字与生命同价啊!
我祈祷上苍让我活着 , 哪怕是当牛做马 , 哪怕是苟延残喘也要让我活着 , 活着看到那一天!即使要我死 , 也要让我变成精卫鸟 , 我要衔来所有的思念 , 所有的盼望 , 所有的泪水 , 所有的怨恨去填补那段断裂了的历史 , 让所有的亲缘血脉都相通 , 让生着的人 , 死了的魂去圆了他们的梦 。
我是幸运的 , 在一个很美很美的早晨 , 当我惊喜的知道封闭的堤坝终于决口了的时候 , 我便迫不及待地涌到潮头 , 我终于实实在在地紧紧拥抱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
母亲瞎了 , 是哭瞎的 , 盼瞎的 。 可她说她的心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我 。 呵 , 像这样的母亲还有多少呢?
我想 , 我仅仅是我吗?我拥抱的也仅仅是我的母亲吗?”
1989年6月 , 舅父带着舅母及小儿子再一次回到故乡 。 他盛赞故乡空气新鲜 , 环境优美 , 乡情淳朴 , 表达了叶落归根 , 永远与父母在一起的愿望 , 并且得到家人的一致赞同 。 不料 , 回到台湾后 , 舅父便被中风光顾 , 卧床不起 。 我们给他寄去些药 , 舅父竟奇迹般康复了 。 也许是大喜过望 , 为了向家人证明他又可以回家了 , 竟以七十高龄和一颗孩童般的心 , 骑着自行车逛街 , 结果酿成大祸 , 给车撞了 , 虽经抢救 , 但已无力回天 。 不久 , 舅母也随他而去了 。
舅父是带着遗憾走的 。 他念念不忘祖国统一 , 让亲人团聚 , 让血脉相连 。 舅母告诉我 , 舅父临终前诵读了陆游的《示儿》 , 最后一句他重复了无数遍 。
遵照他的遗言 , 我们将他的骨灰葬在屋后的山顶 , 面向东海 。 终有一天 , 他会看到他的愿景变成现实 。
(文/蔡小平)
- 一个人的长征:追寻孙子
- 谢朓出守宣城考论(上)
- 元宵节的由来与传说
- LeBron 17 Low为什么低帮还要减配?
- 自编教材评审的标准是什么
- 古人VS地震,整个人都不好了
- 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人良多启示!
- 先访文家市,再探耀邦故居
- 评职称课题最后一名有用吗
- 徐向前,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