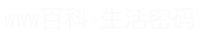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郁长发船图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包世臣像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陶澍像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李筠嘉《春雪集》书影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今上海植物园内黄母祠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募建黄婆祠捐疏》书影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
→沙船停泊图
王健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区真正获得广泛重视的转折点是在清道光六年 , 而且与江苏巡抚陶澍等人组织的漕粮海运密切相关 。 鸦片战争前 , 地方士绅和沙船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正共同主导着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 , 这种新型的绅、商结合的方式跟传统时代是迥然有别的 , 也是当时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突出表现 。
黄道婆崇拜的历史及道光六年请祀事件
众所周知 , 黄道婆信仰是上海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地方信仰之一 , 根据元末文人陶宗仪和王逢的记载 , 元末时黄道婆最先将海南一带的棉种和纺织技术带入乌泥泾 , 繁荣了地方经济 , 因此在她逝世后 , 乌泥泾当地士人“感恩洒泣”而共葬之 , 并为其立祠 , 以志纪念 。
但事实上 ,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 , 乌泥泾黄道婆祠屡废屡兴 , 影响范围并不是很大 , 其中除了明代成化年间曾由上海知县刘琬复建外 , 其余几次均是在乌泥泾本地士绅 , 特别是龙华张氏的主导下加以修建的 。 直至清代乾嘉年间 , 才有记载说当时上海城内渡鹤楼西梅溪弄也有所谓黄道婆祠 , 但根据乾嘉年间上海人褚华在《沪城备考》一书中的描述 , 该祠中所奉神像“如二十余女子 , 群呼之黄娘娘” , 因此也有可能并非黄道婆 。 而嘉庆《上海县志》直接就说该祠实为黄姑庵 , 所供奉的神灵为织女 。 后来王韬在《瀛壖志略》中也据此认为“先棉与黄姑 , 当别为二矣” 。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区真正获得广泛重视的转折点是在清道光六年 , 而且与江苏巡抚陶澍等人组织的漕粮海运密切相关 。
当年由于运河阻塞 , 江苏巡抚陶澍在上海主持漕粮海运 , 获得极大成功 , 150余万石漕粮经海路 , 历时不到两月即抵运天津塘沽口 , 漕米无所损失 , 史称“为都下所未见 , 中外庆悦” , 这是清代漕运史上的一件大事 。 参与这次海运的沙船均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 , 据说其中大号沙船就有1562艘 , 对上海而言 , 其实也是清代中期以来江南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上海的一次大展示和大预演 。
此次事件后 , 上海士民进一步饮水思源 , 将海运的成功归功于作为地方神灵的黄道婆 , 认为“沙船之集上海 , 实缘布市 , 海壖产布 , 厥本黄婆” , 所以黄道婆的功绩 , 已经远远超出“生养吾民”的范畴 , 而是有功于国家社稷 , 是“海运功臣” , 于是部分地方人士联合申文上疏 , 请求将黄道婆列入国家祀典 , 由官方加以祭祀 , 以示庄崇 。
但根据当年包世臣所撰《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的记载 , 这次请封最终却因“上官指驳 , 格于入告”而功败垂成 , 此后直至道光十年再次提出申请时 , 才得偿所愿 。 但关于道光六年请祀事件的具体过程 , 由于史料不足征 , 因此至今无从考据 。
笔者最近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获睹《募建黄婆祠捐疏》一种 , 陋见所及 , 应是至今为止黄道婆研究者所未曾寓目之史料 。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清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联名请求将黄道婆列入国家祀典的申文、从知县到督抚等各级官员关于此事的文移辩驳 , 以及地方士民的再次回应等等 ,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该次请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相关问题 。
江苏学政辛从益的质疑
由《募建黄婆祠捐疏》可知 , 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联名呼吁将黄道婆祠列入祀典的请求得到了从江苏巡抚陶澍到上海知县许榕皋等大部分地方官员的支持 , 主要持不同意见者为时任江苏学政的辛从益 , 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质疑:
首先 , 他认为无法确认黄道婆是否上海本地人 。 因为根据《辍耕录》的记载 , 只是说“国初有一妪自崖州来 , 教以纺织之具云” , 并没有明确说她就是上海人 。 如果严格根据当时国家祀典的规定 , 非本地出生者是不宜列入官方祭祀系统的 。
其次 , 当时棉花生产不仅盛行于南方 , 在北方亦“皆有此种 , 特为茂盛” , 似乎很难与黄道婆联系起来 。
再次 , 他认为当时往来于上海的海船 , 主要从事洋货贸易 , 其中只有部分船只“贩运木棉” , 因此将黄道婆称为“海运功臣” , 有言过其实之嫌 。
辛从益的质疑有部分的合理性 , 尤其是关于黄道婆籍贯的问题 , 直到今天仍然是聚讼纷纭 。 但他的后两点质疑理由实则却正反映了当时清朝一般地方官员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不了解与某种程度上的隔膜 。
因为正如后来上海官绅的回应所言 , 明清以降 , 北方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种植棉花 , 但是却“不能为布” , “皆有南方织成贩运” , 所以“北土吉贝贱而布贵 , 南方反是” , 而黄道婆的功绩不仅仅在引入棉种 , 更在教人纺绩 , 由此形成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 。
另外 , 辛从益认为云集于上海的海船主要从事洋货贸易的说法也并不全面 。 事实上 , 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 , 受益于太仓浏河港淤塞等原因 , 上海正逐渐取代稍北的浏河 , 成为南北洋贸易中心 , 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棉布和饼豆市场 , 东北豆货南来 , 江南棉布北往成为一种常态 , 大量的沙船因此而集聚于上海 , 正是这些适合航行于北洋的沙船后来成为了漕粮海运的主力 ,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 , 上海士民将黄道婆视为“海运功臣”并不为过 。
还值得注意的是 , 道光六年前后 , 江南漕粮征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浮收”问题 , 苏州、松江一带征收一石漕粮往往会多收四五斗 , 甚至六七斗 , 作为漕粮运输的补贴 , 由此引起地方士人的反弹 , 发生所谓“告漕”“闹漕”事件 , 被地方官府弹压 。 针对类似事件 , 辛从益作为学政 , 认为应该约束地方官员的权力 , 维护士子利益 , 因此与主张严惩的江苏巡抚陶澍产生龃龉 。 而黄道婆的请祀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 , 所以辛从益的阻挠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意气之争 。
黄道婆入祀推动者
《募建黄婆祠疏》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让我们得以确认了道光六年推动黄道婆进入祀典者究竟有哪些人 。 因为毛岳生在道光十年的《上海县黄婆祠记》中曾经提及 , 道光六年 , 最初上书推动黄道婆入祀者有十四人 , 其姓名均载于碑阴 。 但由于历年久远 , 碑碣无存 , 因此关于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 , 至今无从查考 。
而根据《募建黄婆祠疏》的记载 , 当时联名具禀者分别为“户部员外郎李林松、刑部主事张惇训、光禄寺典簿李筠嘉、太常寺博士李钟元、都察院经历毛振勋、贡生候选教谕瞿应绍、诏举孝廉方正举人杨城书、布政司经历李心泰、布政司经历朱增慎、布政司经历王揆、廪生莫树堉、廪生郁松年、监生徐渭仁、生员陈瓒”等十四人 。
以上十四人中除陈瓒外 , 其余生平事迹大致可考 , 通过考察这些人的身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 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黄道婆请祀的背景 , 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上海城市社会特质 。
总体而言 , 这些联名具禀者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比较典型的地方士绅 , 包括李林松、张惇训、瞿应绍、杨城书、莫树堉、徐渭仁、王揆等 。 这些人大多出身正途 , 有着进士、举人或者国子生的身份 , 但同时对当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敏锐的见解和较深的介入 。 比如李林松为乾隆六十年进士 , 嘉庆《上海县志》主纂 , 他在道光六年以前就曾经向苏松太粮道汤藩提出了雇募沙船 , 推行漕粮海运的建议 。 再如王揆本为国子生 , 但却“熟悉洋情” , 在道光六年的海运中出力尤多 , 事后得到了陶澍的大力赞赏 。
第二类是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地方士绅 , 包括李筠嘉、李钟元、李心泰等 。 其中李心泰曾祖李长禄、祖父李士达均为商人 , “为贾楚越间 , 家日以饶” , 李钟元曾祖李泓也曾在苏州阊门一带经商 , 李筠嘉则是清代上海著名的藏书家 , 其先世也同样经营商业 , 所以累积了很多资产 , 能够供他搜罗珍本秘笈 。 考虑到明清时期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 他们先人所从事的很可能就是棉布贸易 。 比如与李筠嘉等同时代的褚华在《木棉谱》中就曾提到其家族从六世祖开始便从事棉布贸易 , “秦晋布商皆主于家” , “其利甚厚” , 由此富甲一方 , 或可以为佐证 。
第三类则是直接从事棉布贸易的海商、沙船商 , 其代表者为毛振勋、朱增慎和郁松年 。 陶澍在道光六年海运事竣后的上疏中特别提到了毛振勋和朱增慎二人 , 指出他们在海运之初便“将自置沙船承运米二万余石 , 并将应领水脚银八千余两捐出充公” , 因此对其大加赞赏 。 而朱增慎和郁松年本人便出身于嘉道间上海著名的船商家族 , 其中朱家开设沙船商号“朱和盛” , 有“朱半天”之称 , 郁家开设“郁森盛”号 , 当时民间谣谚称郁家为上海“城中首富” , “多号多船又多屋” 。
可见 , 这些人都与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另外 ,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 , 他们之间在平时就以各种形式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 比如李林松主纂嘉庆《上海县志》时 , 便曾邀请张惇训、莫树堉、徐渭仁、李筠嘉、李心泰等人参与编纂 。 此外 , 他们还通过诗酒文会来维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 当时上海县城内由李筠嘉所修筑的吾园在嘉道间便是此类活动的中心之一 。 由李氏主编的《春雪集》一书汇集了上海地方士绅在吾园内集会时的诗歌唱和之作 , 其中便包括了李林松、瞿应绍、莫树堉、郁松年等人的诗作 。 所以 , 后来在道光六年以吾园之半辟为黄道婆祠并不是偶然的 , 而他们将黄道婆视为“海运功臣” , 进而联名请求将其列入祀典的申文或者也曾经在这个园子里进行过商拟 , 也是可以想见的 。
上海地方绅、商的合流
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 , 这样一个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在当时的上海地方社会运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 比如嘉庆二十五年 , 朝廷疏浚吴淞江 , 由各地县令甄选地方人士担任董事 , 负责相关事务 , 当时上海县有董事四人 , 分别为陈焕、李心泰、李筠嘉和朱增慎 , 后三者的身份上文已有所考释 , 而陈焕同样也是当时上海县内著名的商人 , 并乐为善举 。
此外 , 嘉道间上海城内最为重要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和这一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 比如李心泰的祖父李士达便是上海育婴堂的创建者之一 , 而李心泰本人则参与了另一个慈善机构——同仁堂的创建 。 根据道光十一年的《上海同仁堂征信录》记载 , 当时李心泰和陈焕任该堂司总、瞿应绍负责赡给老人 , 郁松年负责施棺 , 与朱增慎为同族的朱增沂和朱增惠亦分别执掌义冢和赡给老人之事 。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 , 英军逼近上海县城时 , 上海县令刘光斗与城内绅商计议守城策略 , 据时人乔重禧在《夷难日记》中记载 , 当时参与商议的有上海城内所谓大董八人 , 分别为瞿应绍、曹洪集、金树涛、沈希辙、朱增慎、朱增惠、郁松年和徐渭仁等 。
可见 , 鸦片战争前 , 地方士绅和沙船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主导着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 , 这种新型的绅、商结合的方式跟传统时代迥然有别 , 也是当时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突出表现 。
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 , 清代松江、上海地区科举状况逊于周边 , 何炳棣先生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乾嘉以后 , 随着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港口 , 大部分人力资源都被转投入了经济领域 。 即使是那些曾经金榜题名者 , 也纷纷弃古文而趋经济 , 比如那位领衔禀请将黄道婆列入官方祀典的李林松 , 在其晚年便认为八股时文乃至古文、经学皆不足言 , “学者终当求实用也” , 这样的认识应该是绅、商逐渐合流的思想基础 。
当然 ,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乾嘉以降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 而以沙船为媒介的棉布贸易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 在这一过程中 , 黄道婆作为一个信仰符号 , 或许可以被视为能够将不同的绅、商群体联合在一起的粘结剂 。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 曹操有14个老婆,12个是抢来的寡妇,一代枭雄为何爱抢人妻?
- 朝圣大昭寺,为了心中的信仰,为了一生的朝拜
- 他和蒋介石是亲家,一生拥有老婆12个,90岁还娶18岁女孩生下一女
- 为什么说婚后要听老婆的话?这是我听过最赞的答案!
- 差点灭种,一场战争男人锐减不足3万,为发展一个男人要娶4个老婆
- 【我眼中的优秀共产党员】付仕义:一颗初心 一生信仰
- 历史第一 信仰队NiP距离1000图胜仅差一图
- 此人是何应钦嫡系将领,因占领别的老婆被老蒋罢官,并说:永不录用
- 潘金莲的黑化之路:是被王婆设套?还是与西门庆你情我愿?
- 终评 |《光荣时代》:见历史,见考据,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