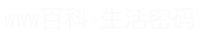汪荣祖追忆何炳棣:其人其学及其清华梦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汪荣祖追忆何炳棣:其人其学及其清华梦

汪荣祖追忆何炳棣:其人其学及其清华梦// //
汪荣祖(左)与何炳棣先生(中)合影 。 资料图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名师如云、图书充足 , 何炳棣本人又极为用功 , 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源 , 力争上游 , 在课业上追求完美 。 他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 , 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年至1937年间的清华”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刘之杨
前不久 , 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作客清华大学 , 与在校师生分享了他与何炳棣先生间的一段忘年交谊 , 并追忆了这位已故史学大家的为人之道、治学之思及其对清华大学、对祖国河山的深切眷恋 。
尽管汪先生本人如今也已年近八十 , 但谈起这位亦师亦友的故人 , 汪先生仍然兴致勃勃 , 妙语连珠 , 毫不掩饰其对何先生的敬意与赞赏 。
初见与初识
汪荣祖与何炳棣初见于1958年 , 当时汪荣祖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读大学二年级 。 那是何先生首次访台做学术交流 , 故而场面盛大、一座难求 。 不少老师坐在前排聆听 , 学生更是挤满了演讲厅 , 汪荣祖正是其中一名 。
据汪荣祖回忆 , 初见何炳棣 , 感觉其南人北相 , 长得人高马大 , 在讲台上一边演讲 , 一边走来走去 , 显得颇为从容自信、魅力十足 , 让人印象深刻 。
不过 , 初见之后 , 两人便没有了直接的交集 。 尽管何炳棣曾经回忆说 , 那场讲座的听众中 , 有未来知名史家汪荣祖和他的未婚妻陆善仪 。 但实际上 , 当时 , 汪荣祖还只是在史学中蹒跚学步的本科生 , 陆善仪也还只是他的同学 。 因此 , 汪荣祖打趣说 , 这里何先生怕是有些“后见之明”了 。
直到1981年的秋天 ,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 , 汪荣祖在这次会议上才与何炳棣正式相识 。 此后 , 一段长达30余年的情谊再没有间断 。
除了学术交流以外 , 汪荣祖与何炳棣私交甚笃 。 汪荣祖在讲座中提及 , 何炳棣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荣休之后 , 应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邀请出任讲座教授 , 而汪荣祖的父母均住在尔湾 , 故而自己与何先生时相过从 。
旅外学者的爱国情怀
众所周知 , 何炳棣是一位旅外学者 , 其在早年间于清华大学完成学业之后 , 便旅居海外 , 继续深造 。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祖国的热爱与关切 。
正是在1981年的这次会议期间 , 何炳棣借机游览长江 , 亲手拂弄江水 , 感受祖国河山之温情 。 汪荣祖眼疾手快 , 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
一年之后 , 何炳棣专程寄信给汪荣祖说:“蒙摄扬子江边濯手一照 , 至感至感!波兰天才音乐家肖邦远赴巴黎时 , 曾携故乡沙土一袋 。 余以炎黄子孙 , 一亲长江之水 , 正此意也 。 ”一位旅外学者的心境跃然纸上 。
对此 , 汪荣祖评价 ,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境 , 何先生身处新旧交替的大转变时代 , 亲历动荡中国的内乱外患 , 特别是日本之侵华 , 让他对饱受战火摧残的祖国越发关切 。 他原想学有所成之后回到清华任教 , 承先启后 , 大展史学宏图 , 但因时局突变而只得滞留异域 。 在此情况下 , 何先生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史学研究中 , 至今仍是唯一一位当选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中国史家 , 这足见其作为炎黄子孙的一颗赤子之心 。
有人说 , 历史学家应该是中立的 , 不应该对任何国家乃至自己的祖国怀有感情 , 否则将影响他对历史的认识 。 但汪荣祖不这么看 , 他举例说就像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劳克一样 , 他既是两卷本《封建社会》的作者 , 没有人能够否认其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 , 同时他也是虔诚而伟大的爱国者 。
布劳克曾评价自己 , 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 , 完全沉浸在法国的精魂和传统中 , 这使他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自由呼吸 。 可见史学家的爱国情怀与其史学素养并不直接相关 。
何炳棣也是这样 , 长期旅外的经历加之中美两国间的历史“封锁” , 使他对故国倍感思念 。
清华岁月与学术启蒙
何炳棣自1934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 可以说 , 他是在清华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卓越的人文环境中 , 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启蒙 。
汪荣祖说 ,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名师如云、图书充足 , 何先生本人又极为用功 , 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源 , 力争上游 , 在课业上追求完美 。
何炳棣跟随刘崇鋐学欧洲近代史 , 从雷海宗学习中国通史 , 从陈寅恪学习隋唐史专题 , 并且为了提高自己的外文水平 , 每天清晨坚持朗读、背诵《罗马帝国衰亡史》 。
此外 , 何炳棣也极重感情 , 他与雷海宗教授师生间情谊最笃 , 旅外数十年仍念兹在兹 。 尽管相隔万水千山 , 沟通不便 , 但仍经其多方探询后取得了联系 。
何炳棣不忘将上世纪50年代在海外发表的论文邮寄给雷先生 , 雷先生也欣喜地作了回应 。 师生间的通信收录在何炳棣的回忆录中 , 读来十分亲切 , 令人动容 。 何炳棣也曾亲自撰文 , 用去颇多篇幅来纪念雷海宗先生 , 阐发先师之潜德 。
清华大学带给何炳棣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享受 , 让其在60余年后仍然念念不忘 。 他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 , 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年至1937年间的清华 。 ”
学术抱负与用功之道
除却上述 , 清华大学还为何炳棣提供了一点重要的学术助力 , 即为其确立了“向大处进军的宏愿” 。 汪荣祖评论道 , 何先生的学术抱负极大 , 而他的勤奋与成就更增加了他的自信 , 让他不作第二人想 。
“何先生可以说是在美国最有成就的中国史家 。 ”汪荣祖曾有此言称赞 。 不过 , 何先生意犹未尽 , 风趣地说:“‘可以说’是对‘最’的怀疑 。 ”
汪荣祖在讲座中还提到一个小插曲:何炳棣曾给自己测算八字 , 结果“他的八字好得不得了 , 可与苏东坡的八字相媲美” 。 当然 , 何炳棣并非迷信 , 只不过这更加增强了他的学术信心 , 坚定了他的宏伟目标 。
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 , 何炳棣开始计划留学 。 留学在当时已经成为“新科举” , 为当时学子跃龙门所必须 。 但新科举之难相较于旧科举 ,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 而且留学费用很高 。 自费留学除了富家子弟外 , 平民家的孩子几无可能实现 , 故而公费留学的竞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
何炳棣于1940年第一次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考试 , 只有经济史一门学科可考 , 结果以些微分差落榜 。
过了两年 , 何炳棣第二次应考 。 谁知这次考试颇为波折 , 先是西洋史一门可能被取消 , 后来确定没有被取消之后 , 又因战事仍频而一拖再拖 。 何炳棣好不容易在开考前三个月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 依靠长久以来积攒的实力 , 一举成为当科状元 。
考试通过之后 , 何炳棣于1945年抵达纽约 , 开启了漫长的旅学生涯 , 读诗阅世自此转移到了北美 。 他选择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博士论文 , 对此他精选导师 , 把课程的研读等事情都安排得很好 , 并注重口语练习 , 所以在口试中表现优秀 。 后来何炳棣回忆这段经历 , 也还颇为自得 。
这并不是何炳棣自夸 。 在其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完成之际 , 何先生的导师盛赞这部论文为一项“值得自豪的成就” 。
不仅如此 , 何炳棣的博士论文还是一个转型的开始 , 他自己将这种转型称为“跃龙门” , 即从研究英国史转向中国史 。 汪荣祖就此评价道:这部史料充沛、具有思维魄力的论文 , 为何先生转向中国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用西洋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史 , 有丰盛的实际经验可据 , 对何先生来说 , 不再是空话 。
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与反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何炳棣的这种转型不仅是其个人研究对象的转变 , 还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的发展 , 即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 , 但又保持传统历史学研究的严谨与扎实 。 汪荣祖称赞何先生是当今利用社会科学 , 结合传统考证方法 , 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 其论文以及专刊莫不如严谨的社会科学报告 。
之所以何炳棣会有如此成就 , 汪荣祖分析说 , 这一方面与何先生很早便立下大志有关 。 何炳棣特别强调选题 , 他本人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也说其平生治史素重选题 。 可以说 , 细枝末节的考据或者无关痛痒的研究 , 他是不做的 。
另一方面 , 也在于何先生的勤奋 。 汪荣祖回忆 , 何先生曾多次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该能用大刀阔斧 , 也应该能用绣花针 。 这就是说 , 既要有宏观的理论 , 也要有多维度的细密的考证 。 何先生每进行一个新课题 , 都要先自学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 甚至与该领域顶尖学者通长途电话进行讨论 , 颇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
正是本着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 《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明清人口史论》《明清社会史论》等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 。 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注重社会科学理论与史料考据的结合 , 打破汉学研究杂货铺式的陈规陋习 。 尤其是《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 , 何炳棣自言其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最为丰富的一本书 , 也是被很多学人效仿的一本书 。
不过 , 到了晚年 , 何炳棣在与汪荣祖的信函中曾自我反思:“但此书(即《明清社会史论》——笔者注)问世若干年后 , 蓦然回首 , 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 , 最主要的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可靠史料 , 因而显得理论往往华而不实 , 容易趋于空谈 。 ”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何炳棣的这段反思 , 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社科理论可以解释其各个面向 , 每一种社科理论或许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上作出深刻的解释 , 而一旦想要铺展开来 , 在史料上便会出现抵牾 , 所谓的深刻即会流于片面 。 这恐怕也是中国古代那些史家们乐于记述而不乐于归纳的原因之一吧 。
责编:高恒涛
- 一堂特殊的党课:20岁参军 九旬老兵追忆挺进大别山
- 居里夫人后人追忆钱三强:他是我父母学生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
- 珍贵老照片 | 追忆毛主席生前感人片段
- 追忆红色经典
- 追忆红色经典——《清平乐·六盘山》的诞生
- 在麻城追忆“红军干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 在麻城追忆“红军干娘”
- 追忆历史 展望未来
- 当代女作家白落梅散文《江南三大名楼之三·岳阳楼追忆》,请欣赏
- 寻遍天下,何处才是长安?再不保护古建筑,我们的后代去哪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