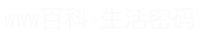维舟:庄子写“庖丁解牛”仅仅是为了宣扬养生之道吗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维舟:庄子写“庖丁解牛”仅仅是为了宣扬养生之道吗
由于“庖丁解牛”的故事被收入《庄子·养生主》一章 , 一直以来 , 历代注解多以为庖丁是借解牛为喻 , 来阐述个人顺应自然、养生长寿的道理 。 如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说:“夫养生非求过分 , 盖全理尽年而已矣 。 ”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认为“养生主”篇“主旨在说护养生之主——精神 , 提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 , 而庖丁解牛的故事则“以喻社会的复杂如牛的筋骨盘结 , 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依乎天理’(顺着自然的纹理) , 并怀着‘怵然为戒’的审慎、关注的态度 , 并以藏敛(‘善刀而藏之’)为自处之道” 。 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则认为全篇是从“循乎天理 , 依乎自然”出发 , “使精神不为外物所伤 , 最后达到享尽天年的目的” 。
但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历史语境 , 恐怕难免会怀疑这样的解释有几分凿枘不入 。 张文江在《<庄子>内七篇析义》中已经表达了困惑:“解牛与养生有何干系?郭象曰:‘以刀可养 , 故知生亦可养 。 ’文惠君之所得究竟如何 , 当深思之 。 ”他对之存而不论 , 在此我们不妨试想:庄子为什么要写下这样一个故事?

维舟:庄子写“庖丁解牛”仅仅是为了宣扬养生之道吗// //
《大秦帝国之裂变》中的魏惠王
这里需要注意到故事中常被忽略的另一个人物:文惠君 , 庖丁正是为他解牛的 , 那番哲理也是对这唯一的听众而发 。 一般认为 , 此人便是魏惠王(前369-前319年在位) 。 在庄子所生活的战国初期 , 魏国最先强盛 , 魏惠王声望极高 。 邯郸之难(前354年-前351年)后 , 魏国“伐楚胜齐 , 制赵、韩之兵 , 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 , 末尾所指即魏惠王于前342年举行的逢泽之会 , 当时东周昭文君代表周天子与会 , 宋、卫、鲁等“泗上十二诸侯”也应召朝见 , 当时魏惠王还没有称王 , 《战国策》说他打算“复立天子” , 即在诸侯中重新树立周天子的权威 , 他再以辅佐天子之功 , 挟天子以令诸侯 , 成就一代霸业 。 但他试图扶持小国、削弱大国的举措 , 最终导致的却是与各大国四面树敌 , 在齐、赵、秦等接连攻伐之下 , 韩、宋等中等国家也渐次离心 , 魏国无法支撑 。 在相国惠施劝说下 , 前334年魏惠王“变服折节而朝齐” , 与齐威王互尊对方为王 , 史称“徐州相王” , 魏国的霸业自此终结 。 到他晚年 , 情形更不利 , 被迫对崛起的秦国采取守势 , 前322年又由于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策略失败 , 不得不采纳秦相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的策略 , 起用张仪为魏相 , 惠施被逐走 。
庄子与惠施均是宋人 , 如果庖丁也是宋人 , 那么庄子知道并记下此事就更顺理成章了 , 《庄子》一书中提到的宋人特别多 ,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认为:“盖庄子居邑 , 本在梁宋间 , 其游踪所及 , 应亦以两国为多耳 。 ”据《庄子·秋水》记载 , 惠施任魏国相国的十五六年间(前336/5-前322) , 庄子就已和他相识 , 著名的“濠梁之辩”大约也在此时 。 《史记》明确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 据此推想 , 庄子所了解的很可能是霸业已终结的晚年魏惠王 , 而庖丁解牛或许也正在此时 。 庖丁以解牛为喻 , 强调“缘督以为经” , 顺物之性 , “依乎天理” , “因其固然” , 这样才能以最小阻力达到最高境界 。
可以想见 , 在经历了盛极而衰、霸业成空的魏惠王听来 , 对庖丁的这一番话会有更深的感慨 。 他感慨:“吾闻庖丁之言 , 得养生焉 。 ”正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指出的 , 在先秦文献的术语中 , “全生/性”、“养生/性”、“害生/性”这些词 , “性”最初是指“活到‘天’赋予人的生命期限的能力 , 也许因使用过度或外来危害而受到伤害” 。 也就是说 , 要遵循天道 , 克制、有限度地使用力量 , 切勿用力过猛 , 最终适得其反 。
但那何尝只是“养生”而已?治国之理也是一样 。 道家的一贯观点就是“无为”才能“大治” , 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 , 我好静而民自正 , 我无事而民自富 , 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 以此参照 , 魏惠王的霸业恐怕正好相反 , 是太过有为、好动、多事、多欲 , 之所以劝喻魏惠王 , 正因战国初期的各国国君中 , 以他最为黩武 。 清人林云铭《庄子总论》:“养生主言人心多役于外应而贵于顺 。 ”可谓片言居要 。 庖丁只是含蓄地引而不发 , 借此表明:您原先太过崇尚强力 , 结果引发邻国敌意而反受其害 , 只有顺天应人 , 遵循自然之理 , 才能事半功倍 , 无为而治 。 所谓“帝王之功 , 圣人之余事也 , 非所以完身养生也 。 今世俗之君子 , 多危身弃生以殉物 , 岂不悲哉!”(《庄子·让王》)
虽然很多人都将庄子的道家哲学当作是一种人生态度(如陈引驰《无为与逍遥》) , 而只将儒法作为中国的两大政治哲学流派 , 但实际上 , 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哲学 , 只是表述得更为含蓄 。 历史学者陈苏镇曾说:“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看 , 先秦诸子在理论层次、研究方法、观察角度等方面往往不同 , 但它们阐述的大多是关于如何‘治’国、‘治’天下的学问 。 这些学问通常包括人性论、治国方略、历史观、宇宙观等不同层次的内容 。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庄子的道家哲学 , 它能够存续下来 , 正是因为能够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社会政治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 就此我们也能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何道家恰好在庄子的时代兴起?这恐怕是因为 ,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 , 才会激发出这样一种对技术文明和权力政治的反思 , 而庄子所出身的宋国正是复古主义的大本营 。
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 , 知识分子还不可能像印刷术出现后的近代西方那样有大批潜在受众 , 所谓“诸子出于王官”通常都被理解为各家学说出自宫廷机构 , 但反过来或许也意味着 , 当时这些学说的潜在听众其实都只是政治精英 。 诸子百家 , 从孔子到孟子、墨子等等 , 更不必说法家 , 大多争相游说君主采纳其学说 。 这些政治上层最关心的 , 显然是治国理政之道 , 因而先秦诸子在很大程度上多是政治哲学 。 同样的 , 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 , 庖丁的哲理也是说给国君听的 。
虽然《庄子》常以出世哲学的面目出现 , 但重回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体会到:他所说的原本都是有具体关怀和指向的 。 庄子所处的是一个剧变的时代 , 面临的是从古未有的深刻社会危机 , 这伴随着社会整体秩序的重整 , 对先秦诸子百家来说 , 所关注的重心也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才能重新安顿好天下人 , 解决这一危机 。 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指出 ,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社会本身的失范 , 连“什么人应处什么位置”等基本原则也已受到挑战;他注意到道家也在回应这一问题 , 但却认为它“把重点放在个人 , 多于社会 , 这明显地与儒法墨诸家不同” , “道家的终极关怀 , 是于乱世中找寻个人的自我救赎” , 认为“道家的旨趣不在规范层次” 。 但事实上 , 道家也追求社会规范 , 只是它主张这一社会规范是依赖一个自发的、无需规范的自然秩序 , 并且 , 这也不是说完全不作为 , 而是看到当时的混乱纷扰 , 正是过度崇尚力争所带来的 。
第一个使用“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术语的法国18世纪经济学家魁奈曾提出 , 经济要完全受“自然法则”(即今天所说的“市场”)调节 。 他认为 , 所有欧洲和中东诸帝国都盛衰无常 , 唯有中国是例外 , 而“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连续的高度繁荣 , 无疑是源自它对自然法则的遵守” 。 他着重强调 ,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的法则 , 而非人为创造的封建秩序 。 这种对“自然法则”的重视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是:硬要逆自然秩序而动 , 是无法长治久安的 。 但“自然”并不易于达成 , 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作为 , 借用王尔德的那句著名俏皮话来说:“表现得自然 , 这是一种很难获得的姿态 。 ”
庄子以上古圣人的名义所提出的自然、无为 , 被广泛地误认为是一种消极、倒退的思想 , 但这恐怕是在进化论视角下的误会;在他那个时代 , 这一观点倒不如说是某种“传统的发明” , 在他之前无人这样系统地提出这一套观念 , 这其实是创新 。 先秦诸子往往借用“德”、“仁”、“孝”等旧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新观点 , 所谓“旧瓶装新酒” , 葛荣晋在总结“道”之探究传统时 , 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道’字虽然在古文献中已屡次使用 , 但是作为哲学范畴 , 则始于老子 。 ”诸子争鸣正体现出那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立场 , 基本伦理价值的根本原则都是由激烈的讨论所塑造的 , 新的思想本身无法独立于当时的社会条件 , 而对它的有意识追求又推动了社会观念变革 , 只不过先秦时人们惯于使用的方式是对旧传统予以新阐释的方式来推动 。
正如日本学者户川芳郎所指出的 , 先秦思想家有一种从自然中求得作为人间社会法则根据的倾向 , 并认为只有“人类社会按照那种自然秩序进行日常运营时 , 才能实现天与人调和的平安世界” , 最终秦汉王朝的建立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巨大帝国的复杂运行 , 当然就是统治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 , 而天地的秩序(即自然运动的法则)被想定为这种行为最根本的基调 , 认为通过对此的正确认识 , 毫不违背地顺应 , 就能使现有的政治体制及其机能得以存续 , 就可以把社会和人间引导到和平的世界 。 ”
在当时的乱世中 , 儒道法代表着当时对社会基本原则的看法 , 且都主张这符合为社会所接受的“自然秩序” , 据此可以达成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长远目标 。 如果建立的这个秩序不能顺应人的本性和自然需求 , 那么很可能无法被承认具备足够的合法性 , 终将行之不远 。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 , 能施行这样一个符合天下人愿望的理念、重建理想秩序的王者 , 就将成为“定于一”的圣王 。 诸子所争论的只是采取什么原则来重建秩序 , 在光谱上 , 道家的“道”最注重自发 , 法家所秉持的“法”强制性最强 , 儒家的“礼”则相对居中 。 当时的各派学说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都在争取一个能采纳己方的思想体系、进而建立自己心目中理想秩序的政治人物 , 最终儒法的胜出 , 均意味着世俗价值观压倒了道家那种带有神秘化倾向的观念 , 不过这并不是完胜:因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发展表明 , 道家和阴阳家的观念大量渗透进《春秋繁露》等著作中 。
但不论如何 , 这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从混沌和无序中创造出秩序的 , 并不是神或与神的契约 , 而是国家力量 。 正是政治权力给社会赋予了形式和规范来整理困顿 , 并成为控制潜在混乱的手段 。 在这过程中 , 道家并不像后人所误以为的那样只关注自我救赎 , 它其实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秩序” , 只是庄子所提出的是一整套包含了人生哲学和政治思想在内的整体理念 。 只有当它在“得君行道”的竞争中失败之后 , 道家才被广泛理解为一套明哲保身的养生哲学 。
- 你不知道的李清照:除了写诗,还是赌神和酒神
- 古人VS地震,整个人都不好了,康熙带头,纷纷写下忏悔书
- 困难总能解决。但是自欺欺人,隐瞒实情,那就完蛋了| 写在历史边上
- 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散文《三月雪》
- 新历史小说之“新”:书写被历史删除的价值观丨文化客厅
- 袁世凯儿子,写得一手好字!
- 张灵甫留一招后手,一旦得逞,孟良崮战役或被改写,粟裕轻松破解
- 改写人类历史的火山!比原子弹猛8000万倍!
- 王瑞来:《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
- 光明时评:苏轼会写诗为文,还会治水?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