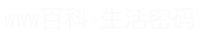太原唐声晋韵:永远的清水河

太原唐声晋韵:永远的清水河// //
一 羞涩之苦
文/刘忠义/作家
其时 , 我11岁 , 在五台县高洪口乡河口村读高小 。
有一天母亲给我稍来干粮 , 是4个糠窝窝 。 几天后如厕 , 多时“迟滞不下” , 上课铃响 , 还未解决 , 一直蹲到第二节课后 , 闻潮水般涌来的同学 , 我上羞下涩 , 换一处靠墙的坑 , 向隅而蹲 , 直至第三节课后 , 我依然在厕 , “凝眉不决” , 掩面躲过可能的关注和询问(羞呢) , 千般努力 , 无可奈何 , 煎熬着等敲响了第四节课的铃声 , 我抽起裤子出了厕所 。 但羞于启齿请假 , 决计逃学 。
河口村离我家10华里 。 那时无公路 , 我顺着清水河河道 , 彳亍向下而行 。 河湾田里的玉米刚刚秀缨 , 泛白渐红 。 拣起五色的鹅卵石用水洗过 , 更加艳丽 。 后来我才知道 , 这一年的11月5日 , 在距离苏联专家撤走82天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 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的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而参试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竟然也在挨饿——骆驼刺掺沙枣的玉米面窝窝蘸着盐水 , 也吃不饱 。 许多人都浮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半年多了不吃肉 , 周恩来连茶也不喝了!全国都在艰苦奋斗!坠意强烈时 , 我就躲进玉米地里 , 蹲 , 甚至用柴棍在战略处捣咕 , 如此三凡五次 , 总不能解决 。 回家后 , 母亲给我喝了一灯盏篦麻油――那时麻油很少 , 我们只吃蓖麻油和花椒籽油 , 但直到晚上还是“攻克不动” 。 我记得清清楚楚 , 天已大黑 , 我蹲在厕所道上 , 父亲举着“油便”照明——小煤窑里窑工专用的一个鸡形铁制装置 , 中空 , 用时装电石加水 , 鸡头处可喷出火焰照明;鸡尾处是长柄 , 窑工背煤出入陡窄的夯道时往往用嘴刁着 。 母亲也蹲了 , 低眉用手抠 , 一点一点地抠 。 我困了 , 就半直起腰来停一会 , 继续蹲下 , 足足有一个钟头 , 母亲用手给我排除了 。 母亲指着地上的秽物说:“你看 , 像沙子!”
那时 , 早上是一两玉米面的两大碗稀粥 , 清得能照相 , 自己有什么再吃点什么 。 中饭是自己的干粮 , 糠窝窝、菜蛋蛋、豆渣、土豆、南瓜 , 伙房负责给蒸 。 第四节课一下 , 同学们一窝蜂地飞向伙房 , 生怕自己的口中食被人夺走 。 记号是有的——在土豆上刻了名字或拴个红头绳什么的 , 但错取或故意抢取的事经常发生 。 干粮都卷在被子里 , 夏日三天就起毛 , 没一个人舍得扔掉一个的 。 丢失干粮的事男女寝室里每天都会发生 。 “偷牛贼”的骂声不绝于耳 。 有几个学生是“惯偷” , 被人打骂时 , 低眉束手眼色怯 , 至今历历在目 。 瑶子村的孙秀林 , 石盆口的季秀成 , 秋荷村的张反林 , 南沟瑶的张金堂 , 许多面黄肌瘦的小儿穷相 , 记忆犹新 。 有一天 , 逮住了一个“偷牛贼” , 竟是一位早已做古的张姓老师 。 张老师是北大贤人 , 模样很帅 , 风流倜傥 。 好给学生改名 , 记得曾将南沟瑶的“改换”、“引根”分别改名为“惠梅”、“惠兰” 。 不信鬼神 , 他曾把观音庙上关老爷身上的红袍揭下来做了裤衩 。 张老师当时的巧言辩词曾令幼时的我愤概 , 可以后每每想起 , 只是心酸了 。
天放曰:岁月悠悠未敢忘 , 开宗明义第一章 。 肥环瘦燕知微妙 , 仙风道骨验肝肠 。 庄子曾云斯有道 , 毛公难言此存艰 。 本是刻不容缓事 , 五谷廻路快哉乡 。

太原唐声晋韵:永远的清水河// //
二 永恒的记忆
文/刘忠义/作家
河口完小有个做饭的 , 叫王清和 , 我们那时叫他大师傅 。 他中等个儿 , 方脸薄唇 , 大眼虚眉 , 约模40岁吧 。 走路如风 , 干活利落 。
伙房里有一盘炕 , 菜刀形 , 很窄 , 比一支单人床稍宽些 。 睡我和张金堂两人 。 我俩是伙食委员 , 负责称米面下锅 。 每早 , 大师傅来了我们还未起床 , 他一进门总是把手插进被窝说:“温温手 , 温温手 。 ”说时就挠我们的庠庠 , 抚我们的小鸡儿 。 庠得我们乱滚乱叫 。 那时我们都不穿裤衩 , 赤条条地扭曲、别动、蜷缩、叠落、拍打 。 他笑着 , 一边挠一边说:“叫你不起 , 叫你不起!”我们眼流生泪、浑身无力了 , 方才作罢 。 然后他就生火造饭——拾柴拾炭 , 涮锅添水 , 进进出出 , 风风火火 , 一会儿屋里就冒气了 。 他边干活边催 , 我们还是不起 , 就说:“说起就起快快起 。 ”边说边就掀开被窝 , 又要挠我们 。 一时 , 锅响了 , 屋里蒸气袅袅 , 该下米了 。 我们起床 , 按人头 , 一人一两玉米面 , 称几斤下锅后 , 我们上早自习去 。
早晨就是这一两玉米面的稀饭 , 中午多半是学生带的干粮 。 有时也用玉米面蒸点菜蛋蛋或糠窝窝 , 每逢这时 , 他总会弄两个小蛋蛋或小窝窝 , 小大如梨 , 悄悄给我俩吃 。 我们心虚 , 只能偷吃 。 偷吃也没地方 , 伙饭里不安全 , 除了学生 , 老师们也常常到伙饭里转悠蓄吃 。 有一次实在无奈 , 我们俩只好到厕所里偷吃 。
王清和喜欢我俩 , 更喜欢我 。 他三不六九地把我叫到他家里 , 给我做拌汤吃 。 白面拌汤里煮了土豆条条、豆腐条条 , 油煎葱花 , 有时还荷包一个鸡蛋 。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最好最香的饭 。
王清和老家是山教神的 , 不知道何时迁住河口 。 他有一儿一女 , 女儿叫春梅 , 小我三两岁 , 总叫我哥 。 儿子我没见过 , 七、八岁时死了 。 他总说 , 我长得与他死去的儿子一模一样 。 回家与我母亲说起 , 母亲说 , 他是真心喜欢你 , 还说想认你做干儿呢 。 母亲不愿意认 , 按农村的习俗 , 认了干亲 , 婚丧嫁娶都要走动搭礼 , 我已经有两个干妈了 , 太麻烦 。 渐渐地我也懂事了 , 就称呼他清和伯 。 以后我在耿镇上初中 , 或瑶子村看我妹妹 , 路过河口总要去看望清和伯 。
在我当兵期间 , 婶死了 。 婶嘴唇有壑 , 俗称兔唇 , 单眼皮 , 话音沙哑 , 极善良 。 我每次去家 , 总是急急地给我做饭 。 生怕我饿着 。 我1973年第一次探家时她还活着 , 我去河口看望同学就住她家 。 清和伯后来得了中风病 , 我还从云南给他寄过一次药 。 又一年探家看他时 , 他给村里看店房 , 檐台上晒着太阳 , 目光迟滞 , 表情冷漠 , 唯唯诺诺 。 我低徊而愧 , 感慨良多 。 我1975年结婚 , 婚后与妻子还看过他一次 , 如此算来 , 他是1975年后去世的 。 享年几何 , 我并不记得 。 我知道 , 春梅就嫁在本村河口 , 我和妻子说过 , 要去看看春梅的 , 但一直也没有践行 , 想起来就不安 。
在那饥饿的年代 , 清和伯与婶给了我最真诚最珍贵的爱 。 我去耿镇念初中了 , 还一样关照过我上高小的弟弟忠怀 。 这些 , 我都不会忘记 。
天放曰:此时相忆笑貌近 , 百姓衣裳君子心 。 正是天灾兼人祸 , 恰逢国穷更家贫 。 先生肝肠贮锦绣 , 后来兄弟受宠恩 。 半个世纪不相忘 , 书出不忘坟头吟 。

太原唐声晋韵:永远的清水河// //
三 道不远人
文/刘忠义/作家
1962年秋天 , 我上初中了 。 耿镇中学 , 离家40华里 , 父亲决定送我 。 我们村考上三人 , 另有罗文华、胡德奇 。 三个父亲背着铺盖卷 , 我们空手 , 沿清水河逆上 , 走累了就坐下来 , 席地盘腿而坐 。 文华的父亲示范着说:“腿盘紧 , 歇得好 。 ”腿脚反复动作 , 嘴角夸张 , 眼色盈盈 。 父亲寡言而笑 , 贪婪地吞吐着小兰花 , 头顶的烟雾袅袅而欢欣 。 石盆口至耿镇的公路大概1968年才通车 。 三年里六个假期 , 往返我们都是步行 。 三年后 , 我到五台城上高中 , 离家55华里 , 公路是有了 , 也没坐过一次车 。 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是一月六元 , 票价是三毛 , 是一天半的伙食费呢 。 从家到校 , 爬上鸽子岭后就走过40里了 , 常常是脚指上的血泡也撞破了 , 生致致地痛 , 饿得腰儿弯弯 。 可从没觉得苦 , 记忆里全是快乐 。 求学之路 , 我并不是最远的 , 最远的要数孙计生、白贵良等同学了 , 有一百多里呢 , 也从不坐车 。
最豪爽和快乐的是一次夜行 , 从耿镇回家 。 一学期四个多月 , 第一次这么久远离开父母 , 放寒假了 , 归心似箭!记不得是怎么相约和几时上路 , 也记不得确切的人名和确定的人数 , 只记得是一大群!耿镇以降、清水河下游可能村村都有 , 最远的是杨安和、白双秀等陈家庄乡周边的学生了 。
一群学生 , 一河冰 , 一河风 。 风号着 , 豪爽而凌咧 , 先是顺风 , 乘风在冰上滑行 。 夜漆黑 , 冰面上黄土隐隐 , 小跑几步 , 半蹲了身子 , 打一个滑串 , 摔倒了 , 两眼生泪 。 一河呼唤 , 一河笑声 。 仰望夜空 , 星河灿烂 , 豪情满怀 。 先驱者的滑串抹去了冰上的黄土 , 冰新且亮 , 后来者的滑串更猛烈也更迅疾了 , 摔得也更惨重些——“铛”的一声 , 后脑勺着地 , 只觉得后脑勺里“针、针、针”作响 , 双眼直冒火星 。 手背一揉 , 眼睫毛上硬硬的全是冰霜 。 后来我常想 , 农家的孩子头耐 , 得不了脑震荡 。 一时 , 不记得是谁提议了 , 说要“等一等” , 等齐了 , 黑蔟蔟一片 , 一群人集合了 , 要唱歌 。 “来吧来吧年轻人 , ”只记得这一句 。 还有一首是“我们是草原的雄鹰 , 飞翔在草原上 , 把青春献给包钢 。 ”夜空璀璨 , 群山默然 , 我们热血沸腾 。 到河口村时 , 变成了逆风 , 吹得睁不开眼、出不了气 , 张大了嘴换气时 , 大风却不失时机地往肚子里灌 , 灌进了气管 , 岔了气 , 灌进了肚子 , 透心凉 。 那时戴有耳朵棉帽或皮帽的极少 , 单帽易落 , 许多人“帽子、帽子”地叫 , 却是再也逮不住了 。 风吹在腿上、吹在身上 , 衣裳贴骨了 , 向是无数只无形的手在捏你 , 同学们三三两两扭在一起 , 咧且着前行 。 进了村 , 我家的大门还未开 , 正叫时 , 听到院子里水桶和扁担钩子的“光铛”声 , 我知道 , 父亲要挑水了——清水河特惠我村 , 入村时河道辗转蜿蜒到了南山根底 , 中间冲积成一片上百亩的水田; 冬天要到南山底的老棺崖处破冰取水;因此家家户户要早起挑水的 。

太原唐声晋韵:永远的清水河// //
开了门 , 父亲看了看我又抬了头看天 , 说:“走了一夜?”我顺着父亲的眼睛 , 也去看天:东方微呈鱼肚白 , 几个固执的星星还在隐隐闪烁 。 进了家 , 母亲心痛地浑身抚摸 , 才发现 , 我右腿膝盖上有个口子 , 一条裤腿上的棉花全飞了 。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 , 这一年10月至11月间 , 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 , 并大获全胜 。
天放曰:快哉此风天地动 , 敢问宋玉是雌雄?鲁阳轻挥戈返日 , 共工怒碰地陷东 。 海枯自有填海鸟 , 天破岂无补天丁 。 古人幽默我浩叹 , 叔向贺贫非矫情 。
唐声晋韵编选
- 太原小井峪唐代壁画墓神秘面纱正在揭开 墓主是恒州刺史郭行,活了92岁!
- 在“最后的芮国”赏周风遗韵
- 普洱茶,为何要学武夷岩茶讲岩韵?
- 三百文物呈现古芮国“周风遗韵”,国博展陕西刘家洼考古发现
- 【康博公馆】六艺文化节之古韵茶道
- 品武夷岩茶,何谓“岩韵”或“岩骨花香”?
- 济南故事——匡山石韵:见证日月,韵承历史
-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太原档案馆向社会征集档案资料
- 器韵 | 纯净到极致的“釉”惑
- 人文荟萃古韵新颜——走进历史文化名城兴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