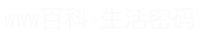栾保群《梦忆》拾屑︱报国寺松、直头饿死与犬声如豹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栾保群《梦忆》拾屑︱报国寺松、直头饿死与犬声如豹
一、报国寺松
卷六《鲁府松棚》云:“报国寺松 , 蔓引亸委 , 已入藤理 。 入其下者 , 蹒跚局蹐 , 气不得舒 。 ”
天下叫报国寺的寺院不知凡几 , 此处说的报国寺是哪一座 , 诸家注本未见有说明者 。 我不愿回避 , 心想张岱既然有了“气不得舒”的感受 , 那就在张岱视履所及的范围去找吧 。 张岱一生北至泰山 , 南至浙江的天台、宁波一带 , 找来找去 , 于是试注如下:“以‘报国’名寺者甚多 , 此当指杭州凤凰山之报国寺 。 元废南宋宫殿 , 于原址造五寺 , 此其一 。 ”我猜测此报国寺在杭州凤凰山的理由还有一个 , 就是此地多松 , 报国寺不远就有个“万松”牌坊 。
但这注是错的 , 因为缺少一个必要条件 , 即遍查方志 , 也找不到此地有类似“入其下者 , 蹒跚局蹐 , 气不得舒”的矮松 。 相比之下 , 此松是否为张岱所亲见 , 则非必要条件 , 如果这“报国寺松”非常有名 , 张岱就是没见过 , 也不妨写在文章中吧 。
抛弃旧的思路之后 , 便豁然明白 , 原来此松近在眼前 , 就在张岱的山水知己刘同人的《帝京景物略·报国寺》一文中 , 其名为“偃盖松” , 共二株 。 此报国寺位于北京广安门内大街路北 , 全名为大报恩慈仁寺 , 建于元代 。 刘侗记道:
送客出广宁门(即今广安门)者 , 率置酒报国寺二偃松下 。 初入天王殿 , 殿墀数株已偃盖 , 既瞻二松 , 所目偃盖松 , 犹病其翘楚 。 翘楚者 , 奇情未逮 , 年齿未促逼也 。 左之偃 , 不过檐甃 。 右之偃 , 不俯栏石 。 影无远移 , 遥枝相及 , 鳞鳞蹲石 , 针针乱棘 。 骇叹久 。 松理出 , 盖藤胫而蔓枝 , 旁自变量丈 , 势不得更前 , 急却而折 , 纡者亦轮转 , 然无意臻上也 , 被于地则已耳 。 人朱柱支其肘 , 乃得局蹐行影中 。
所谓“藤胫而蔓枝”“局蹐行影中” , 正是张岱所本 。 而张岱《山艇子》写怪竹也全用此篇笔法 , 读者对比来看 , 自有会悟 , 可知张岱对刘侗此篇的烂熟和喜爱 。 又明蒋徳璟《记报国寺》亦记此二松:
双松偃盖 , 皆数百年物 。 东者可三四丈 , 有三层 , 西则仅髙二丈 , 枝柯盘屈横斜 , ?数亩 , 其最修而压地者 , 以数十红架承之 。 移榻其下 , 梳风幕翠 , 一庭寒色 。
蒋徳璟对此松的感受便与刘侗大异其趣 , 他觉得躺在下面乘凉是很舒服的 。 不让我直腰 , 我就躺着 , 也算自得其乐之一法 。
张岱有志以一己之力修撰明史 , 却未能有机会北出泰山一步 , 明朝的都城只能在他的想象之中 。 而明末浙东史学的另一大家谈迁 , 倒是有机会一入京华 , 但一介书生 , 为人作幕 , 困顿无聊 , 他在《北游录》中自言:“口既拙讷 , 年又迟暮 , 都门游人如蚁 , 日伺贵人门 , 对其牛马走 , 屏气候命 , 辰趋午俟 , 旦启昏通 , 作极欲死 , 非拘人所堪 。 ”又言: “惟报国寺双松 , 近在二里 , 佝偻卷曲 , 逾旬辄坐其下 , 似吾尘中一密友也 。 ”谈迁眼中的双松“佝偻卷曲” , 正是自己身世的影子 , 所以引为密友 , 以寄悲情 。 这大约是报国寺双松最后一次见于明代文人笔记 。 入清之后 , 游报国寺者只是夸谈“窑变观音” , 那时的双松应该早就没有了吧 。
我常想 , 谈迁是海宁人 , 与绍兴仅一江之隔 , 他和张岱只相差几岁 , 怎么竟连一面之缘都没有呢?
二、直头饿死
《梦忆》自序云:“瓶粟屡罄 , 不能举火 , 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 , ‘不食周粟’ , 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 ”
这句话并不难懂 , 只是说从自己困饿荒山的体验想到了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境况 , 应该是食无可食 , 活活饿死 , 至于司马迁说的义“不食周粟” , 那不是后人妆点的好话而已 。 但再三读过之后 , 总觉得张岱此语有言外之意 , 不可轻易 , 因为它直关张岱的生死取舍 。 而此语既出 , 张岱则不死也 。
自“弘光乙酉秋九月”至次年丙戌正月 , 张岱一直处在人生最低谷 。 其实乙酉年的春天弘光小朝廷已经覆亡 , 鲁王朱以海渡过钱塘江 , 称“监国” 。 张岱很快参预抗清武装的组织活动 , 意气风发 , 奔波驱驰 , 一面数上鲁王笺表 , 筹划方略 , 一面招募兵马 , 亲自输送到鲁王驻地 , 指望能在浙东凝聚成一股抗敌力量 。 但事与愿违 , 昏庸无能的朱以海固无足论 , 要命的是此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多是宵小之徒 , 其中包括一些东林末流 。 这个小政权的实力其实比县衙门大不了多少(守江的方国安军根本不听朱以海节制) , 现在却要硬撑起一个朝廷的架势 , 因为那些宵小把鲁王居为奇货 , 指望靠“从龙”捞取“开国元勋”的资本 。 他们见张岱与朱以海的前代有些瓜葛 , 深怕张岱动了他们的奶酪 , 便编造谣言 , 对张岱极力排挤 。 到九月初 , 张岱觉得谤毁丛身 , 性命可危 , 便再上鲁王一表 , 告辞而去 , 从此流亡于剡县 , “披发入山 , 骇骇如野人” 。 “瓶粟屡罄 , 不能举火” , 正是此时境况 。
一面是抗清之事无为 , 一面是处于饿死的边缘 , 这时的张岱就身陷“活着 , 还是死去”的哈姆雷特怪圈了 。 他很想走好友祁世培的道路 , 舍生取义 , 一死了之;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 , 是撰写十年尚未完稿的《石匮书》 。
《石匮书》对张岱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 他从崇祯初年就立志要修明史 , 而且他不以科举为念 , 就是想以此书立身后名 。 可是现在明朝已经亡了 , 《石匮书》却仍未成稿 , 在他看来 , 此书不成就等于白活了一世 。
而舍生取义呢 , 舍生容易 , 反正没饭可吃 , 但“义”在何处?前辈王思任、刘宗周都是绝食而死 , 义存千古 。 可是人家是有食而绝食 , 自己却是已经无饭可吃 , 死也是“直头饿死” , 何必去冒充义士殉国呢?就是后人追认自己为义士 , 也不过是名不副实的“妆点语” , 怎么能自欺欺人呢?自序中“直头饿死”一段 , 张岱说得真是胸襟坦荡 , 义利兼顾 , 他明指夷齐 , 实指自己:如果此时死掉 , 辗转沟壑一饿莩而已 , 于国谈不上义 , 于己也谈不上利 。 人不可苟活 , 也不能苟死:以死欺世盗名固不可 , 以死逃避责任也同样不可 。
只读《梦忆》会让人误解张岱是个“太平闲人” , 其实他很看重功名 。 但正因为他把功名看得重 , 所以也最讲真实无欺 , 要实功 , 要名副其实的真名 。
有朋友问我 , 在那一年 , 如果没有《石匮书》的牵挂 , 张岱会不会寻死呢?我说:当然不会 。
三、犬声如豹
《梦忆》自序云“五十年来 , 总成一梦” , 似是对自己前半生的清算 , 而《梦忆》的最末一篇却记了一个真实的梦 。 此篇仅见于《梦忆》一卷本 , 砚云甲编本一卷本无题 , 科图钞本则题为《平水梦》 , 比后来人所题的《祁世培》要好 。 张岱把这篇放到编末 , 我认为与写作时间的早晚无关 , 是想为此篇赋予特殊意义:平水之梦开启了他的后半生 。
这梦发生在顺治三年初的荒村野店 , 扑朔迷离又清晰如画 , 是张岱一生文字中少有的灵异记录 , 而且透出了浓重的鬼气 。
由于这梦写得很逼真 , 梦中的祁世培所言不但正中张岱所想 , 而且很有预言性 , 所以有不少朋友问我:这梦不会是张岱编出来的吧?我的看法是 , 张岱在当时的境况下 , 完全可能做这样一个梦 。 常言道“梦由心造” , 梦中的一切 , 都反映着张岱的心理酝酿和意志抉择 。 是出山继续追随鲁王 , 还是埋名屏迹去完成《石匮书》 , 这正是张岱近几个月徘徊犹疑的心事 , 而且正如前一篇所说 , 他已经大体拿定主意 , 所以出现在梦中并以预言的方式由祁世培说出 , 也是很自然的事 。
所以祁世培对张岱前途的指示 , 还算不上此梦的灵异 , 因为那里有张岱的心理暗示发生着作用 。 令人注目的是梦中对抗清大局的悲观预言:
世培曰:“天下事至此 , 已不可为矣 。 尔试观天象 。 ”拉余起 , 下阶西南望 , 见大小星堕落如雨 , 崩裂有声 。
张岱做梦是在顺治三年初 , 而西南抗清政权中 , 广州的绍武帝是在年底才败死 , 桂王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十几年后才消亡 , 祁世培指示天象 , 这就很像是鬼魂的前知了 。 张岱深知鲁王小朝廷的虚弱和无所作为 , 把复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西南武装上 。 梦中群星堕落的天象 , 等于让张岱彻底绝望 , 其震动是巨大的 。
然后祁世培洒然而去 , 接着是梦中的“犬声如豹” , 张岱惊醒 , 大汗浴背 , 此时又听到“门外犬吠嗥嗥 , 与梦中声接续” 。 为什么在祁世培出门后突然“犬声如豹”?因为犬看到了异物 。 异物是什么?是祁世培的鬼魂 。 而梦中的犬吠这时又转变为现实中的犬吠 , 梦境就是现实 , 梦中的祁世培就是真实来访的鬼魂 。 这证明了什么?梦中好友的话都是忠臣灵鬼的预言 。
- 《圣斗士星矢》重病的伊利亚斯为什么还能对冥斗士产生重大威胁?
- 刘先银悟《论语》中国文明古国离不开一个人,孔子都很佩服他
- 部编版八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电子课本】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圣斗士星矢》史昂也触摸到女神之血,为什么寿命没有延长?
- 视频//【雪石朗诵】刘辉《我是曹操》
- 视频//【雪石朗诵】刘晖《我是曹操》
- 徐绍基《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杂论
- 一部颂扬两代人献身抗痨事业的纪实文学《奇医神药》(连载六)
- 说说《水浒传》中的婚俗文化:娶妻、纳妾、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