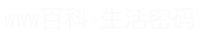钟焓读《大元史与新清史》③︱多语种文献间的表达差异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钟焓读《大元史与新清史》③︱多语种文献间的表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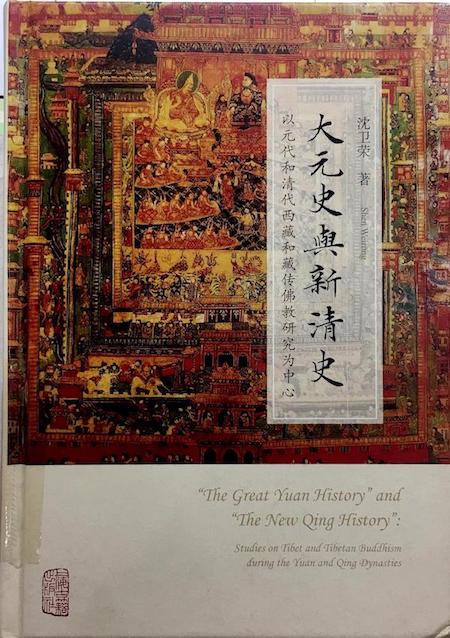
钟焓读《大元史与新清史》③︱多语种文献间的表达差异// //
《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 , 沈卫荣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 305页 , 58.00元
最近国内的清史学界已就如何看待清史研究中的汉文史料与非汉文史料关系比重的议题 , 掀起了开放性的热烈学术讨论 。 沈教授对此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 。 他根据自己处理不同语种文献的切身经验提醒专业读者 , 对于同一篇文献的不同译本要在慎加比勘的基础上关注不同文本间的内容差异 , 但也不能简单地以各自文本间的字面含义存有差别为由 , 进而彻底否定它们在语境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 尤其是不宜把其中的某种语言文本中的若干有别于其他文本的表述一概断定为当时的史臣有意窜改的结果 (本书259-262页) 。 笔者不是专业清史学者 , 对于浩如烟海的清代多语种文献缺乏像博览史籍的教授所具有的那种直观而又丰富的阅读体验 , 但基于“隔行不隔理”的学术伦理 , 还是深感他的此番提醒和概括精准地命中了问题的要害 。 下面仅以平时接触到的某些个案对沈教授的如上观点试做进一步的证明 。
按照流行的观念我们通常假定 , 当一种文献同时存在汉文和满文或者更多的语言文本时 , 应该有一种文本是最初撰写成文的母本 , 其他的文本则属于由其衍生出来的二次或三次生成的译本 , 所以有关的问题常常被化约为究竟是汉文本还是满文本或者其他文本才是这种原始母本 。 不可否认 , 这种直线思维般的追寻问题的方式在学术研究中确实有它的适效性 。 譬如当涉及康熙后期前往土尔扈特人出使的清朝使臣图理琛根据其出使见闻撰写成书的《异域录》 , 因其在以后刊刻时陆续有满文本和汉文本行世 , 诚然有必要通过比对彼此内容的详略差异来厘定满汉文本的先后次序 。 当然这个问题早已被日本满学家今西春秋解决了 , 他揭示了其在 1943 年偶然发现于北平的刊刻于雍正初年的九耐堂满文本《异域录》应当是最接近图理琛撰写底本原貌的文本 , 其内容常常详细于人们通常引用的四库全书本等汉文本《异域录》 , 稍经对比即知后者在某些具体内容的叙述中有所删简 。 因此 , 我们在利用史料价值十分珍贵的图理琛此书时 , 理应首先参看今西春秋根据九耐堂满文本《异域录》复原的内容相对完善的书面文本(其以《校注异域录》为名在 1964 年出版于天理大学) , 而不宜过度信任虽然容易寓目但文字表达业已有所简化的四库全书本 。
还有一些多语种文献则难于直接从内容的比对或者文体的写作风格等“内证”要素的发掘中确定孰为底本 , 孰为译本 。 即如崇德三年(1638)秋著成的关于沈阳郊外佛寺兴建原委的《实胜寺碑记》 , 其以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 。 显然 ,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实胜寺碑记》最初的文本是用汉文还是满文写成 。 此前德国满学家嵇穆(M.Gimm)教授以为该碑文起初是由大学士刚林用汉文书写 , 然后再被分别翻译为其他三种文字 (其德语论文收入《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 , 紫禁城出版社 , 2003 年) 。 他大体是通过汉文部分在遣词造句上的用语雅训得出这一结论的 。 表面上看 , 这种分析似乎确有一定的道理 。 不过 , 随着相应的清入关前内阁国史院满文档案的系统刊布 , 其中明确提到了关于上述《实胜寺碑记》的撰写及翻译经过 , 即“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 , 学士罗绣锦译汉文 , 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 , 多木藏古希译土伯特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4页) 。 由此可知 , 刚林最先撰就的这篇碑记其实是用满语书成 , 而汉语和蒙古语、藏语一样 , 均属于经过翻译以后形成的二次文本 。 只不过罗绣锦译就的汉语文言文在辞藻用语上尤显典雅近于无懈可击 , 容易给人以其系碑记底本的错觉 。
相对前面这类证据尚属明显的例据而言 , 还有一类更为复杂的情况 。 那就是在某些双语文献中 , 其实不能简单地断定某一文本就是底本 , 而另一文本则为译本 。 在此笔者不妨也列举两个实例以加深读者对此的印象 。 先看第一个例子:
早在后金开国之后的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前期 , 努尔哈赤向民众发布了一份规劝其效忠后金 , 摈弃明朝的昭告文书 。 该文书的汉文刻本收藏于前北京图书馆 , 早在多年以前就被日本满学家今西春秋全文刊布 , 起初被怀疑是努尔哈赤致万历帝的文书 , 以后则被修正为其昭告的对象是明朝辽东一带的军民 。 文告的中心是努尔哈赤援引历史上朝代兴亡的众多实例来劝说汉人相信明朝的气数已尽 , 而后金却在逐渐赢得天命的支持 。 这件重要文献刊布后 , 长期以来学界都深信其劝谕的对象只是针对特定的汉人群体 。 然而 , 上世纪末两位欧洲学者却意外地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发现了该文献的满文文本 , 并进一步将其鉴定为现存时代最早的满文木刻本 , 由于留存下来的入关以前的满文文献数量相对稀少 , 故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显得十分重大 。 (参见[俄]庞晓梅、[意]斯达理:《最重要科学发现之一:老满文写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 , 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六辑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00年 , 第186-191页 。 )
该件文献既然是以满文刻本的形式存现 , 那就表明当初努尔哈赤殷切希望以自己的口吻讲述的这篇文告的内容能够被其境内使用满文的群体所知晓 , 故才将其刊刻发行以广流传 。
此后两位刊布者之一的庞晓梅曾撰文专门考察了该文书的满汉文本的次序问题 , 并以该文献在引用中国历代典故逸事时 , 满文本往往失之少译甚或有所误解为据 , 认为满文刻本实际上是译自汉文本 ([俄]庞晓梅:《满汉文〈努尔哈赤檄明书〉何种文字稿在先?》 , 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 , 709-714 页) 。 这同样是根据内容的详细程度来判定底本和译本的次序问题 。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该文告的具体内容 , 不难发现存在两种情况 , 第一种就是如同庞氏所揭示的 , 在那些大多数内容是汉人熟知的历史典故中 , 汉文本的质量确实优于满文本;可是也存在相反的第二种情况 , 即文告中也有少数事例的发生背景对于满族(或者说女真人)而言才更为熟悉 , 其中满文本关于其的叙述反而又优于汉文本的相应内容 。
这后一类故事与前一种汉人耳熟能详的事例相比 , 多有其自身的语气特征 。 譬如努尔哈赤在讲述前一种事例之后 , 往往还有“尔南朝(nikan si)……”之类的警示性结语 , 而后一类故事则无这种表述;还有一些内容因涉及先前建州女真内部的一些纷争 , 显然满族比汉人更加清楚故事发生的具体背景 。 同时也正因为普通的汉人大众在获读文告时 , 出于对后一类故事缺乏背景知识的了解 , 所以一般不会将其当作重点来阅读 , 故当初在制作满文本和汉文本时 , 往往后一类故事在满文本里的内容更加详细准确 , 相反汉文本中的同样内容则较为节略 , 甚至还出现了粗枝大叶的歧误 。 如其中的一则故事讲述的是努尔哈赤先祖曾经受到女真Giyahu 部的欺凌 , 汉文本径直将后者表达为“有属部人贾胡者” , 容易让人误以为贾胡(Giyahu)是人名而非部名 , 另一则故事则讲述的是女真人中的 Uyunta 氏族与努尔哈赤先祖的恩怨纠纷 , 汉文本却将 Uyunta 按字面意思误译为九人 。 至于 Giyahu 部、Uyunta 氏与努尔哈赤先祖交恶的内容在满文国史院档中也有记载 , 由是可知汉文本在编写过程中出现了上述差池 。 (参见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 , 东京:东洋文库 , 2001年 , 55-56页)因此 , 现在还不能仅凭内容的出入程度断言该文献的满汉文本中孰为底本 , 孰为译本 , 因为误译或少译的情况在两者中均有出现 , 不妨认为满汉文本在制作时依据的是大致相同的口承性资料 , 惟考虑到对象群体的不同 , 所以在文本的编写工作中各有侧重 , 相应地也各有纰漏 。
再来推敲分析第二则实例 。 康熙帝第四子胤禛入继大统后 , 于雍正二年(1724)撰写颁布了满汉合璧的《御制朋党论》 , 通过批判北宋欧阳修为君子正常交往进行辩护的《朋党论》一文 , 严厉警告臣下不得结交党羽 , 朋比为奸 。 日本学者石桥崇雄在对这篇御制之作的满汉文本进行比勘的过程中 , 意外地发现两者之中竟然有一处明显的细节表述上的差异 。 那就是当雍正在文中需要就欧阳修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批判立场时 , 其在汉文本的表述是说 , 假设欧阳修生活在本朝 , “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 , 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 即虽然表达了要严厉批评欧阳修此论的观点 , 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要对其人施以何种惩罚 , 仅仅要达到“正其惑”的规诫教育目的即可 。 然而 , 满文本此处的表述却大不一样 , 充斥着警告意味十分直露的血腥杀气 , 其称如若欧阳修处在今世而倡言此说 , 那么“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参见石桥崇雄:《雍正帝“御制朋党论”研究(序说)——大清国统治结构分析试论的一环节》 , 收入《高桥继男教授古稀记念:东洋大学东洋史论集》 , 汲古书院 , 2016 年] 。 那么为什么满汉文本在这段涉及雍正帝对欧阳修的处置态度的内容中 , 竟然会呈现出如此之大的鲜明反差呢?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御制朋党论》的满汉文本之间存在着底本与译本的差别 , 而是应该承认两者的撰写都是出自雍正本人或者由其直接授意 , 所以对两者在细节表述差异的解释需要更多地考虑满汉文本的各自受众群体以及雍正即位之初时的政治环境 。 从《御制朋党论》不同文本的受众群体来考虑 , 无疑汉文本的读者对象是朝中的汉族大臣 。 而从汉人士大夫群体的观点来说 , 活跃于北宋中期政坛的欧阳修显然是一位宦声卓著的治世纯臣 , 向来被视为道德操守良好的宋代文臣典范 。 尽管他所撰著的《朋党论》一文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过不小争议 , 但从整体上看对其个人的正面形象尚无明显的贬损 。 可以说 , 即使在宋元以后的明清时期 , 欧阳修在儒家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未发生变化 。 因此 , 如果即位不久的雍正此刻仅仅以其撰写的这篇在当下看来明显不合时宜的《朋党论》为借口 , 就要把对其的惩戒拔高到“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的地步 , 那么显然会使在朝的汉人大臣为之惊恐不安 , 从而既不利于新君安抚汉臣群体的情绪 , 更容易使后者在私下里对于君主产生腹诽之心 。 于是 , 雍正帝在写作《御制朋党论》的汉文本时 , 需要尽量压抑其内心对欧阳修此文的愤懑不满情绪 , 转而摆出一副宽宏大量 , 不计较臣工之过的仁君面目 , 以诉诸说理教育的方式促使有朋党嫌疑的本朝臣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从而主动改过自新 。
那么为何满文本的表述又显得如此杀气逼人呢?首先自然是作为满文本《御制朋党论》阅读对象的满人或旗人官僚来说 , 欧阳修其人在该群体心目中的形象必定不像在汉人官员那里那么高大 , 所以严肃处置一位像他这样的汉人文臣 , 从心理情感上来说当不致激起满族官员的明显反感 。 不过更为关键的原因还应归于雍正即位伊始对于时局形势的研判与分析 , 而雍正初年的政治形势在相当程度上又和此前康熙晚期的朝政时局密不可分 。 众所周知 , 康熙朝晚年朝政的最大乱相就是因太子再度被废后引发的储君之位长期空悬的政治难题 , 由此导致对其心存觊觎之心的众阿哥在私下纷纷接交外臣党羽 , 一时形成了密谋夺嫡的皇子各有其党的纷争局面 。 其中声势最为喧嚣者莫过于皇八子胤禩的结党活动 , 致使“皇八子党”的势力一时遍布朝野 , 上有为其深结的贵胄重臣联名为之保奏 , 下有文人名士倾心辅佐 。 当然时为雍亲王的胤禛虽然表面上以“天下第一闲人”淡定自居 , 然而在暗地里同样大肆市恩结党 , 只不过其生性险诈 , 故在行事上更善于矫饰 , 所以终究未像胤禩那样因锋芒毕露以致引起其父的警觉与反感 。 继而胤禛在父皇病故后凭借隆科多、年羹尧等党羽之力一举排除诸兄弟的掣肘 , 如愿以偿地君临天下后 , 倍感焦虑棘手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平息处理康熙晚年遗留下来的与争夺储君之位直接关联的党争遗产 , 以便使自己以非常之手段得来的宝座能够安稳如常 。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 显然有必要将彼时依然环伺在朝的其他阿哥的党羽清理整肃 。 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当初在夺嫡风波上势头最盛的胤禩一党 。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胤禩党羽的构成情况 , 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一个以宗室王公 , 外戚勋旧以及位高权重的若干功臣后裔等满洲高层为骨干的强势政治集团 。 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康熙舅舅佟国纲的长子 , 前朝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清初四辅臣之一的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以及其子阿尔松阿、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后裔苏努乃至传统意义上的八家铁帽子王的部分后裔等 (杨珍:《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 , 也收入前述《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 。 这些出身满洲统治上层(包括像作为皇帝亲戚的被称为“佟半朝”的特定汉军旗人)的党争核心成员多数都在康熙晚期的政局中占据要职 。 此种政治环境的养成则肇始于康熙自三藩之乱后对汉臣群体的猜忌之心终生不曾释怀 , 并且越是到其统治晚年 , 这种无端的猜疑心理就发展得越发严重 。 因此朝中汉官为了避祸 , 平时多主动疏远对军政要事的参预处置 (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 北京三联书店 2015 年) , 所以在康熙晚期朝中“内满外汉”的权力分配格局已经让人洞若观火的政治环境下 , 彼时久蓄夺嫡之心的诸阿哥交结引援的主要对象自然会转向那些握有实权的满洲旗人大员以及地位尊崇的王公勋戚 。 因此 , 彼时卷入皇子党争群体的朝中官员人士无疑是以满人为主 , 而以汉人为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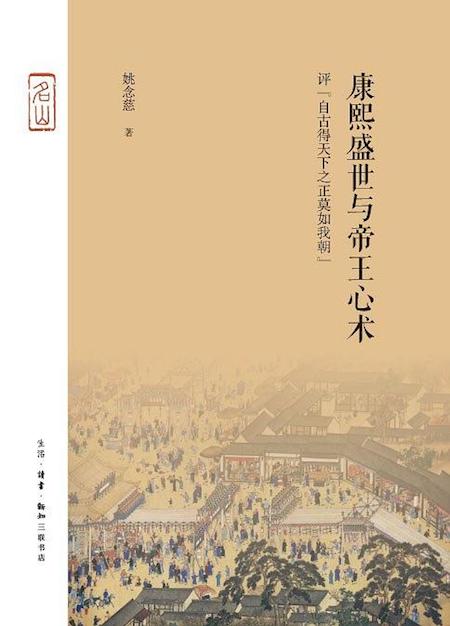
钟焓读《大元史与新清史》③︱多语种文献间的表达差异// //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待到胤禛以夺嫡之争的最后赢家既登大宝以后 ,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将前朝遗留的政治格局清理得干干净净 。 基于人数如此之多的原属胤禩支持者的满洲上层权贵依然占据着朝中的显要位置 , 况且他们又与初登大位的新君素来并不同心 , 这对胤禛试图稳定朝纲的中心政治任务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 。 可是在雍正继位之初 , 他所倚重的年羹尧尚在青海前线处置与和硕特蒙古起事有关的紧急军务以及忙于筹措随后的各项安抚措施 , 同时朝廷在此期间还在与准噶尔汗国一方谋求进行恢复和平的试探性谈判 。
因此 , 在这种外部形势尚不完全明朗的情势下自然不宜立即着手布置那种牵涉面极广的政治清洗 , 以免从根本上动摇政局 。 于是我们看到 , 这位在清代诸帝中最为谙熟帝王两面手法的君主先是采取封赏胤禩等权宜之计以暂时稳住自己的政治对手 , 降至雍正二年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后 , 他便立即通过发布内容语气带有明确惩戒色彩的《御制朋党论》来警告原来党附于胤禩等阿哥的势力集团赶紧认清形势 , 自服其辜以取得新君的谅囿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 尤其是鉴于后者的核心成员多为满族亲贵 , 故雍正在该文的满文本中特地借攻击欧阳修的《朋党论》将这种威吓性的惩戒意味表露得十分直白 , 毫不隐晦 , 其中堪为点睛之句的“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则直接表明了如果满族高层之中有人在朋党问题上已经触碰了新君的底线 , 那么即便此人负有像一代名臣欧阳修那样的声誉与才能 , 自己也会毫不惜才地对其处以杀伐严刑 。 相比而言 , 汉人大臣既然自康熙晚期以来因屡受打压而无足称道 , 甚至后来连康熙本人都公然不讳地声言朝中汉官业已后继无人 , 那么雍正当然没有必要再把清洗的重点扩大到汉臣群体当中 , 以此只要在《御制朋党论》汉文本中稍稍表露一下对欧阳修观点的责罚立场即可使之畏忌君权 , 无需像其在满文本中的表述那样刻意要把清洗党人的政治气氛渲染得格外紧张 。
总之 , 与其说雍正帝此时亮出的那面格外刺眼的“正其惑世之罪”的板子敲打在了早已去世了几百年的古人欧阳修的身上 , 不如说其兴师问罪的箭矢实际上则瞄准了那些于现实中不肯跟自己“一心一德”的满洲亲贵们 。 真不知昔日与其他皇子过从甚密的满族大臣们在读到《御制朋党论》中这句潜台词分外严厉的“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时 , 内心会是一种怎样的惊悚之感?因为正是在同年的早些时候 , 对于依附其他皇子的党人群体早就耿耿于怀的雍正即已“不教而诛”地启动了对于前朝阿哥旧党内的关键人物进行全面政治清算的工作 。 如果将二者联系思考 , 似可认为《御制朋党论》满文本中的上述出格言论正是雍正为其假借去除朋党之名大肆清洗政敌之举的政治宣判书 , 意在点出只要彼辈仍旧执迷不悟 , 那么自己绝不会因为顾忌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出身地位而对之采取即往不咎的宽大处理 , 即使其中有人名声学养堪比欧阳修者也不得侥幸免死 。
这项株连层面极广的被雍正自比为“整理变化”的清洗大狱以后一直延续到胤禟、胤禩于雍正四年秋季相继死于非命之后 。 其间受到惩治的朝中大臣之多 , 仅就党羽最多的“皇八子党”而论 , 兹据王锺翰先生在其名篇《清世宗夺嫡考实》中所做的统计 , 即已多达四十余人 。 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其中受到穷治的满人或旗人出身的要员及宗室竟然是汉人的三倍以上 , 而且遭到清洗的那些满族政要的仕途地位普遍也要高于受惩的汉人同党 , 后者仅有萧永藻等个别人士曾有入仕中央高官的履历 。 看来当初那句惟见于满文本《御制朋党论》内的“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如今在相当程度上确乎变为了现实 。 凡被正法枭首以及遭遇幽禁而死者固不待言 , 纵然侥幸免于一死者也早以戴罪之身纷纷成了惊弓之鸟 , 不啻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 。 随着这一时期新君在满洲统治集团中进行的政治清洗的持续扩大 , 竟至在一时间让最高统治者抒发慨叹 , 忧虑起“近日廊庙中颇乏卿贰满臣”(《清世宗实录》卷五一 , 雍正四年十二月癸未条下) 。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主要波及满族高层人士的政治清算则在无形中成为了催生清廷高官内旗人与汉人官员比例消长的因素之一 。 试检楢木野宣编制完成的数种有关清朝高官任职情况的统计表格 , 从中可见恰恰是在雍正时期 , 汉人出任中央机构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以及地方的巡抚一职上较之上一个十年的康熙晚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 仅在总督职位上汉人官员的比例反倒有所下降 , 然而就总体而言 , 汉人所占朝廷高官的比例仍然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 (参见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满汉并用的全貌》 , 风间书房 1975 年出版) 。 不妨说 , 尚在雍正六年曾静案事发之前 , 导致这位君主朝夕思虑焦灼的政治难题还是满洲旗人政要群体深度卷入的前朝党争问题在本朝的自然延续(包括像稍后的隆、年之狱这类政争余波) , 而非事关满汉对立的华夷之辩 。 至于雍正在《御制朋党论》满文本中发出的毫不掩饰的“朕必杀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这一恐吓性政治信号不仅是皇帝本人已经在悄然动手布置铲除满人党争势力时的真实心态写照 , 也从中映照出胤禛其人对于其他参与夺嫡的阿哥及其党羽素所怀有的绝不宽恕的极度憎恶心理 。 以上即是笔者思考《御制朋党论》满汉文本所见内容差异的一点极不成熟的个人看法 ,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分析某些清朝多语种合璧类文献得以形成的政治性背景因素 。
- 《圣斗士星矢》重病的伊利亚斯为什么还能对冥斗士产生重大威胁?
- 刘先银悟《论语》中国文明古国离不开一个人,孔子都很佩服他
- 部编版八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电子课本】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圣斗士星矢》史昂也触摸到女神之血,为什么寿命没有延长?
- 视频//【雪石朗诵】刘辉《我是曹操》
- 视频//【雪石朗诵】刘晖《我是曹操》
- 徐绍基《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杂论
- 一部颂扬两代人献身抗痨事业的纪实文学《奇医神药》(连载六)
- 说说《水浒传》中的婚俗文化:娶妻、纳妾、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