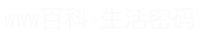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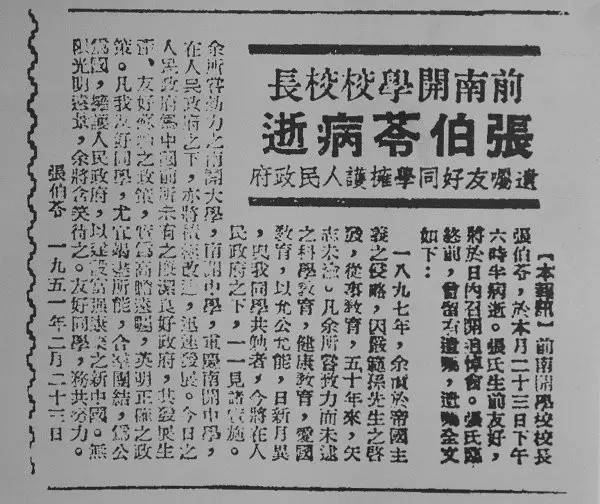
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
(▲1951年2月26日 , 《天津日报》刊登黄钰生代笔、经张伯苓生前认可的遗嘱 。 图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摘要:张伯苓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 , 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 , 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
作为“康梁时代的人”(周恩来语) , 张伯苓在两个政党、两个国号、两条道路、两个命运的决战中 , 无论生前逝后 , 无论主动被动 , 都备受关注 。 他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 , 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 , 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
首先 , 海内外报道冰火两重天 。
大陆反应冷淡 , 只有《天津日报》于1951年2月26日刊载黄钰生代笔的遗嘱 , 题为“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病逝 , 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又刊载他三位儿子的一个79字“哀启” 。 其他大陆新闻媒体沉寂一片 , 无任何综述、评论、纪念 , 更谈不上深度报道 。 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 , 也未公开披露 。
海外却热乎不已 。 港台、美国等地报刊、通讯社深入报道 , 例如《纽约时报》刊发专题纪念文章 , 称其“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 。
其次 , 纪念规格冰火两重天 。
4月8日 , 张伯苓逝世后44天 , 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 , 未公开报道 。 大多数人仍在观望 , 怕受政治株连 。 与会者只有350人左右 , 无高层官员 , “老年人多 , 青年人少 , 穿长袍、西服的多 , 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 。
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司徒月兰、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和杨学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等参加追悼会 。
还好有周恩来领衔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 “同学们发起追悼会 , 周恩来校友领衔 。 出殡之日 , 天津市人民政府 , 奉周总理之嘱托 , 送来花圈 。 ”(黄钰生《关于张伯苓先生遗嘱的真象》)
追悼会结束后 , 天津市委统战部在送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 , 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伧 , 不热烈也不悲壮 , 会场显得很冷清 , 零零落落的 , 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 。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
台湾当局的纪念格外隆重 , 而且比大陆办得更早 。 2月27日 , 蒋介石获悉张伯苓病逝 , 在日记中写下“痛悼无已” 。 3月31日 ,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追悼大会 , 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 。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0卷 , 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年版 , 第53、89页)公祭时 , 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 , 蒋介石亲致祭文 。
第三 , 遗嘱的“真伪之争” 。
张伯苓第二次中风后 , 不能说话 , 但听力可以 , 意识清醒 。 据甄光俊考证 , 经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 ,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按照张伯苓的口吻 , 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常逐句逐字地斟酌了一份遗嘱 。
黄钰生来到张伯苓床前 , 放慢语速读代拟的遗嘱 , 每念完一段 , 张伯苓都点头同意 。 听完全篇 , 他挑起大拇指 , 表示赞赏 。 在场者有张伯苓夫人、儿子锡祚夫妇、儿子锡羊的爱人 。 锡羊的爱人还大声问张伯苓:“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又一次挑起大拇指 。 因为当时张伯苓的手已不能握笔 , 这个遗嘱上没有张校长的签字 。 (甄光俊《张伯苓遗嘱真相》)
1976年 , 台湾南开校友编印《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 , 出现伪造的《张校长伯苓先生遗嘱》 。 主要破绽有二:其一 , 张伯苓行伍出身 , 好用大白话 , 从来不用骈体 , 但“遗嘱”里有“惟始皇阴狠 , 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 , 沐猴宁能成事”之类骈体;其二 , 张伯苓1951年2月14日中风 , 八天后手已不能动作 , 伪造的“遗嘱”注明日期是“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 竟然有张伯苓“签字” 。
1980年春 , 民盟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小组访问黄钰生 , 核实此事 。 黄澄清:“我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多年的同事 , 又是张校长遗嘱的起草人 , 我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 。 ”
第四 , 两岸评价冰火两重天 。
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传记和专著等 , 肯定张伯苓的办学功绩 。 此后 , 每逢张伯苓逢十诞辰 , 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
但他的名字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成了“忌语” , “张伯苓就像一颗流星 , 倏忽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 ”他创立的南开也面临一系列冲击和调整:校歌销声匿迹 , 紫白色的校色久违于校园 , 校训成了历史的陈迹;私立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收管 , 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1952年院系调整 , 拥有文、理、工、商四学院的综合性南开大学 , 萎缩成仅有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当年接收“敌产”而扩展的三处校园 , 又缩回旧有的八里台一块校址 。 (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
南开大学各院系批判张伯苓的调门日益高涨 , 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 , 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 。
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 , 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 。 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 , 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 。 1960年 , 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 (司徒允《逝去的大学|张伯苓之后 , 再无南开》)
(【山水微言·241】 。 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30节 。 )
- 传统节庆:今天正月十三虫王节
- 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乘坐风轮飞跃天堑,这本古书诸葛亮比演义还神
-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 致投资者的一封信
- 西游记中,元始天尊和地仙之祖镇元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 太平天国灭亡时曾国藩造反的话,会有人追随他吗?
- 天津这栋洋楼有百年的风云故事,因为两位人物,让它声名远扬
- 三峡系列六:才访三游洞,又观天然塔,宜昌半日闲,走马观花行、2
- 刘表的碌碌无为,错失争霸天下的良机而成为鱼肉
- 8天屠杀150人!二战可怕的一件衣服,一名逃兵穿上之后,马上化身为魔鬼!
- 元始天尊可以复活门下弟子,通天教主却为何一个也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