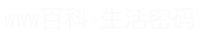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管新生:那年那月那篇小说,画满了圈圈点点
摘要:于我而言 , 记忆海滩上最为美丽的一枚贝壳 , 就是当年我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故事 。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管新生:那年那月那篇小说 , 画满了圈圈点点// //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管新生:那年那月那篇小说 , 画满了圈圈点点// //
有些事情分明发生在今天 , 可你一转身之际可能早己忘却;有些事情分明过去了很多年很多时日 , 可你偏偏却永远无法忘怀 。 岁月的长河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进行着大浪淘沙的游戏 , 尔后在人们记忆的海滩上 , 留下了点点闪光的美丽贝壳——于我而言 , 其中最为美丽的一枚 , 就是当年我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故事 。
1971年10月的一个黄昏 , 想起来那天一定有一缕收获季节的金风拂上了我的脸 。 那天我上中班 , 正在炉子间里汗流浃背地做着生活 。 突然看见厂部政宣组的负责人王载欣笑吟吟地奔了进来 , 让我快去他的办公室接听电话 , 说是《解放日报》社打来的 。 当时我肯定是吃了一惊 , 并且很有些不知所措 , 而周围的工人兄弟们全都激动起来了 。 我清醒过来后 , 才怀着一个初学写作者那种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 , 飞快地来到政宣组 , 拎起了搁在办公桌上的电话话筒 。 电话里是个很亲切的声音 , 先是问我还记不记得他们去年曾经寄给我的一份我创作的反映车间工人生产竞赛的小说校样 , 接着问我现在能否有时间立即来报社修改一下这篇小说 , 最后告诉我他们在这个星期天准备刊出 。 我赶紧请示了一下身边的老王 , 他说他马上和车间里打声招呼 , 还说会给我半天公假的 。 这时电话里的声音才告诉我 , 他叫谢泉铭 , 去报社后直接找他 。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管新生:那年那月那篇小说 , 画满了圈圈点点// //
管新生1970年代初期在上海铝材厂当炉前工 。
放下话筒我才知道 , 谢泉铭曾在电话里反复向老王说明我的创作情况:尽管那篇打成校样的小说稿一年来未见报 , 但作者并未气馁 , 依然一往情深地痴迷于文学创作 , 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他寄来的小说、散文 , 颇有些鲁迅先生所赞扬的那股韧劲和毅力 。 现在报社再度准备发表他的那篇未刊稿 , 希望单位党委能同意 。 接电话的老王奇怪地问 , 一年前为什么没能发表?回答说当初征询单位意见时是“不同意” , 理由是作者一心埋头爬格子 , 自然是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表现 , 所以走的是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 说到这里 , 谢泉铭便用当时的流行语反问老王 , 文学创作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 怎么会是走白专道路呢?老王当即答复说 , 十分赞同他的意见 , 代表单位表示同意这篇小说发表在党报上 , 并且很负责任地说自己也是党委成员 , 有权作这样的表态……
在赶往《解放日报》的路上 , 我自是心潮澎湃 。 我十分感谢这位尚未谋面的编辑老师 , 是他竭力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创作者原本应当拥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 。 我忘不了一年多以前收到小说校样时夜不能寝的情景 , 忘不了自那以后的每个星期天都站立在报栏下痴情地望着那每周一版的《看今朝》文艺副刊、想象着自己的习作变成铅字的振奋 , 忘不了收到《看今朝》突兀寄来的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 立足本职工作 , 继续努力创作出好作品”来信后的极度迷惘和失落……
走进了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那暗红色的拱形大门 , 来到了《看今朝》那间小小的编辑室 , 终于见到了后来扶持了很多大作家小作家并且一直被文人们尊称为“老谢”的谢泉铭老师 。 试想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有生第一回来到了一向被自己认为极其神圣的报社 , 到了极尊重的编辑面前 , 那一份虔诚那一份惶恐是可想而知的 。 谢老师或许是看出来了 , 他先是很随和地与我海阔天空聊了一会工厂的情况 , 尔后才问我将那份小说校样带来了吗?我结结巴巴地说没带 , 还放在家里呢 。 他点点头从办公桌上拿起了一份校样递给我 , 说这就是你的那篇小说 , 你能不能再仔细看一遍有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地方呢?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管新生:那年那月那篇小说 , 画满了圈圈点点// //
谢泉铭(左)和管新生(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
当我看完了后想了老半天还是说不出个子寅丑卯时 , 他抽着烟缓缓地谈起了他的修改意见 , 并且还虚心地征询我的看法 。 后来递给了我一支笔和几页稿纸 , 我就在旁边的办公桌上很认真地修改了起来 。 修改完了给他审阅 , 他看了好一会才说 , 有几处改得很不错 , 有几处仍需再润色一下 。 这时 , 我注意到窗外的天色己经黑了下来 。 他忽然问我晚饭吃过了没有 , 我有些不好意思 , 他却说自己也没有吃饭呢 , 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吧 , 饭总是要吃的 。
吃晚饭的过程谢老师具体和我谈了些什么已然记不清了 , 大抵都是一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吧 。 但有一点至今依然记得 , 那就是他后来一直嘱咐我的要我多读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 。 可惜我至今仍较少涉猎这一方面 , 很有些辜负了他的那一番苦心 , 不然也就不会在创作上如此迟钝如此鲜有进步了 。 这是我每每一回想起来便要汗颜便要心跳加快的一件事 。
再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 , 我的拘谨及不安显然大为改善了 。 孰料 , 谢老师这时却来了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 他突然又取出了一份校样 , 说他其实早己为我改好了 。 让我自己修改一番 , 只是为了看看我的改稿能力而已 。 我看着那份画满了圈圈点点的校样 , 心底里陡然涌起了一股感激之情……
后来 , 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让我铭记了一辈子的话 。 他说 ,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小说见报了 , 就以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很不错 。 其实一篇文章的发表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 , 就拿你的这篇小说来说 , 报社打算发工业题材小说 , 偏偏来稿大多都是农村小说 , 这才想到你积压了快一年的那份校样 , 所以……
三五天后 , 我的这篇名为《竞赛》的一千几百字的小说终于见报了 。 尽管许多年以后的我 , 已经发表出版了近700万字的中长篇小说 , 但是依然永远忘不了那年那月那篇小说 。 因为那是我涉足文学世界的处女作呵 , 尤其是在那个全国文艺刊物大都被牢牢冻结在地平线下面的非常年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 岁月的大浪早已淘尽了诸多的泥沙 , 唯有记忆海滩上的美丽贝壳永久地在升腾着不朽的光彩 。 原来 ,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 都会珍藏着那一份真那一份情那一份缘的……
- 《圣斗士星矢》重病的伊利亚斯为什么还能对冥斗士产生重大威胁?
- 刘先银悟《论语》中国文明古国离不开一个人,孔子都很佩服他
- 部编版八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电子课本】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电子课本(高清版),寒假预习必备!
- 《圣斗士星矢》史昂也触摸到女神之血,为什么寿命没有延长?
- 视频//【雪石朗诵】刘辉《我是曹操》
- 视频//【雪石朗诵】刘晖《我是曹操》
- 徐绍基《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杂论
- 一部颂扬两代人献身抗痨事业的纪实文学《奇医神药》(连载六)
- 说说《水浒传》中的婚俗文化:娶妻、纳妾、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