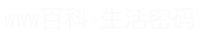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
——张炜引论
文/赵月斌
摘 要:张炜的文学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 他通过千万文字写出了一个异路独行、神思邈邈的“我” , 对这个时代发出了沉勇坚忍的谔谔之声 , 用“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创造了一个天地人鬼神声气相通 , 历史与现实相冲撞的深妙世界 。 张炜是一位天真诗人 , 诗不仅是他的“向往之极” , 而且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基点 , “诗”成为他获取自信、成就“大事”的原动力 。 对张炜来说 , 写作就是一场漫长的言说 , 是灵魂与世界的对话 。 他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生存之道 , 同时也透露出一种以退为守 , 以守为攻的隐逸倾向 。 就像一位从显性世界回到隐形世界的孤独梦想家 , 张炜从非诗的阴影里走向了诗 , 在“渎神”的背景里找到了自己的“神” 。 1
关键词:天真诗人 童年精神 故地情结 孤独梦想家
01
当我们试图讨论张炜的时候 , 不免要考量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 探究他的文学立场和精神向度 , 显然 , 在他的作品中多少常会显露一种高古老派的清风峻骨 , 他的写作虽非金刚怒目、剑拔弩张 , 却从不缺少暗自蕴蓄的幽微之光 , 不缺少地火熔岩一样的“古仁人之心” 。 张炜用他的天真和梦想道说时代的玄奥 , 把苍茫大地和满腔忧愤全都写成了诗 。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张炜不只是以文学为志业 , 更是把它作为信仰和灵魂 。 他认定文学是生命里固有的东西 , 写作是关乎灵魂的事情 。 “写作是我生命的记录 。 最后我会觉得 , 它与我的生命等值 。 ” 对张炜而言 , 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本能 , 就像震彻长空的电火霹雳 , 释放出动人心魂的巨大能量 。 它源于自身并回映自身 , 同时也照彻了身外的世界 。 我们看到 , 张炜的文学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 不仅创造力出奇地旺盛 , 且每每不乏夺人耳目之作 。 19岁发表第一首诗 , 60岁出版第20部长篇小说 , 结集出版作品一千五百余万字 , 单从创作量上看 , 张炜可算是最能写的作家之一 , 而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力 , 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 , 蜚声海内外的汉语作家 。 无论是位列正典的《古船》、《九月寓言》 , 蔚为壮观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 , 还是境界别出的《外省书》、《刺猬歌》、《独药师》 , 以及风姿绰约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演讲、对话等 , 莫不隐现着生命的战栗和时代的回响 。 张炜通过千万文字写出了一个异路独行、神思邈邈的“我” , 对这个时代发生了沉勇坚忍的谔谔之声 , 他用“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 创造了一个天地人鬼神声气相通 , 历史与现实相冲撞的深妙世界 。
“一个作家劳作一生 , 最后写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 。 ” 张炜的全部作品实际就是一部不断加厚的精神自传 。 他就像精于术数卦象的占卜师 , 又像审慎严苛的训诂家 , 总是在“大胆地假设 , 小心地求证” , 反复地推演天道人事的命理玄机 , 稽考家国世故 , 厘订自我运程 。 经过不断的分蘖增殖和注释补正 , 方才写出了一部繁复而丰润的大书 。 这部大书的中心人物就是张炜自己 , 它的主题便是张炜及其时代的漫漫心史 。 如此看待他的一千五百万言似乎太显简单 , 我却觉得这正是张炜的堂奥所在 , 通过这简单的“一本书”、“一个人” , 我们会看到多么浩渺的世界和多么幽邃的人生啊!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世界风云变化 , 但即便如此 , 该言说的还是要言说 。 管他轰的一响 , 还是嘘的一声 , 世界并未真的结束 , 所谓空心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毁灭性的流行病疫 。 人们还是要前赴后继、按部就班地过生活 , 过去讲“苟日新 , 日日新 , 又日新” , 现在说“与时俱进 , 不忘初心” , 以后还是要“时日依旧 , 生生长流” 。 一切总在消解 , 一切总在更生 , 我们能够做的 , 好像只能是抓住当下 , 勿负未来 。 这是一个无名的世界 , 又是一个人人皆可命名的时代 。 面对无所归依的浑浑时世 , 张炜一直是冷静淡定的 。 从开始唱起“芦青河之歌” , 就表现得清醒而克制 , 甚至显得有些保守 ,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对他就是一种褒贬参半的说法 。 但是如其所言:真正优秀的作家 , 是必定走在许多人的认识前边的 , 他们的确具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力和创造力 。 张炜的作品正是走在了前边 , 当我们耽于某种谬妄或迎向某种风潮的时候 , 张炜恰选择了批判和拒绝 , 那种不合时宜的“保守”倾向 , 反而证明了他的敏感:比起众多迟钝的俗物 , 他往往及早察觉了可能的危险——他就是那个抢先发出警报的人 。 当雾霾肆虐演变成无法改观的常态时 , 他在十几年前就描述了这种“死亡之雾” 。 当人们拼命地大开发、大发展的时候 , 他看到的是水臭河枯、生态恶化、“线性时间观”的狭隘短视 。 在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大大解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今天 , 张炜对凶猛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始终持有一种“深刻的悲观” 。 对他而言 , “‘保守’不是一种策略 , 而是一种品质、一种科学精神” 。 因此方可像刺猬一样安静、自足 , 没有什么侵犯性 , 甚至温驯、胆怯、易受伤害 , 却始终有一个不容侵犯的角落 。 他在这个“角落”里安身立命 , 自在自为 , 用长了棘刺的保守精神抵御着躁狂时代的骚动与喧哗 。
真正的作家、好作家是一个朴素的自我定位 , 张炜固然认为 , 我们无力做出关于“时代”性质的回答 , 但他未忘作家的本分就是“真实地记录和表达 , 而不再回避生活” ,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 张炜一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 , 以反潮流的保守姿态对这个天翻地覆的“大物”时代予以决绝的回击 。 他说 , 巨大的物质要有巨大的精神来平衡 , “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 他之所以推崇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 , 就是因为稷下学人留下了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旷世大言 。 就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 ”“说大人则藐之 , 勿视其巍巍然 。 ”“君子之守 , 修其身而天下平 。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 , 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 , 无私无隐 , 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 。 ” 张炜显然也是以这些圣者大言为高标的 , 他认清了大时代的大丑恶、大隐患 , 痛恨“立功不立义”的野蛮发展、异化生存 , 因此才能“守住自己 , 不苟且、不跟随、不嬉戏” , 才能融入野地 , 推敲山河 ,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 。 于此 , 他才更多地牵挂这个世界 , 用诗性之笔写出了伟大时代的浩浩“大言” 。
02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张炜是一位诗人 。 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最早进行的文学习练就是诗 , 后来也从来没有放弃诗的写作 , 写过大量的诗 , 出版了两部诗集 。 事实上 , 作为诗人的张炜不全在于写了多少分行文字 , 更主要的是 , 诗不仅是他的“向往之极” , 而且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基点 。 张炜正是这样把诗写进一切文字的人 , 尽管他常自嘲缺少写诗的天分 , 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 但是从他的作品里总能读出诗的根性 , 不光语言散发着诗的光泽 , 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 整体上也弥漫着优雅凝重的经卷气息 。 张炜像是打破了文体的界限 , 几乎把所有作品都写成了纯美诗章 。
在张炜看来 , 诗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形式 , 更是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 。 所以他用诗的标准评断小说、散文 , 乃至所有艺术样式 。 以诗论艺正是典型的中国式审美维度 , 张炜即认为:中国第一部文人小说《红楼梦》具有“诗与思的内核” , “中国现当代小说 , 从继承上看主要来自中国的诗和散文” 。 他很看重“自己的传统”——中国小说的传统 。 因此 , 不仅要从文本上继承这种传统 , 还要在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 “诗是艺术之核 , 是本质也是目的 。 一个艺术家无论采取了什么创作方式 , 他也还是一个诗人 。 ” 可见“诗”既是张炜的创作指标 , 也是他个人的自我认定 。 “诗人”之于他从来不是普通的职业名称 , 而是一个不落凡俗的高贵席位 。 诗性 , 成为张炜的绝对尺度 , 他执着于诗 , 唯诗性至上 , 以诗性加深写作的难度 , 这也是他的作品大率不失水准的前提吧?
那么 , 何为诗性?何为诗人?张炜曾经申明:诗性不等于风花雪月 , 要知道也有惨烈之诗 。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 诗性不是青筋暴露、肉麻充楞 , 不是卖弄辞藻、撩拨情怀 。 真正的诗性并非文字表面肤浅的抒情或假装激动 , 而是一条内在的血脉 , 它显露于语言又隐匿于语言 , 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诗性是一个类似于密码的东西 , 一开始就植根在人的基因里的 。 ” 这就更有点儿神秘了 , 好像是说诗性本是天生的 , 没有一点儿慧根的人 , 不光写不了诗 , 恐怕连诗里的密码也读不出来 。 他强调诗与生命的关系 , 那种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完全把写诗混同于文字的过度加工 , 所以有人才会把装饰性的、抖机灵的玩意儿吹上天 , 他们不知道诗的最低要求就是真诚而朴素 , 若与真实的生命感受割裂开来 , 哪怕再漂亮的文字也与诗无关 。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张炜深信“诗人才能干大事” , 并且比一般人干的大事更大 , 因为诗人的胸怀更奇特 , 有一种旺盛生命力 。 他把诗人看成了天生异禀、身有大能的特出之人 , 他们所干的“大事”当然也不是可用世俗标准衡量的出人头地、扬名立万之事 , 而是和张炜称道的“旷世大言”相类 , 指的是形而上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永恒之诗 。 “诗人应该具有足以透视无限深处的慧眼 , 应该摆脱个人人格的束缚 , 而成为永恒的代言人 。 ” 张炜曾引述“天才诗人”兰波的这句话 , 以此“反省自己” , “诗人”是他矢志追寻的远方镜像 , 又是他对另一个“我”的一种心理投射 , 他每每对诗人致以推崇 , 每每声言写过好多诗 , 却好像从未认可那个“诗人”就是他自己 。 比如在谈到《忆阿雅》时 , 他一则说它出自真实的记录 , 是“一个为背叛所伤的诗人的自吟” , 转而又说:“我不能说自己就是那个‘诗人’ 。 虽然它以第一人称写出 , 也只是为了有助于自己对诗和诗人的理解 。 ” 张炜此言不虚 , 多读他的作品也会发现 , 他确是以全部的写作走近诗和诗人 , “诗”是他的文学向度 , “诗人”则是和他精神往来的潜在的自我 。
在一篇短文《为吟唱而生》 张炜中简白地表达了他的“诗人观” 。 不难看出 , “为吟唱而生”的诗人正是张炜本人 。 通过自我观照 , 他发现了“我们的诗人” , 通过对诗人的深切探问 , 他走向了生命的澄明之境 。 “诗”成为张炜获取自信、成就“大事”的原动力 , 具有顽强灵魂的“诗人”成为“我们”最需要的时代之赤子 。 在另一短文中 , 张炜再度阐述他的诗观:“诗对于我 , 是人世间最不可思议的绝妙之物 , 是凝聚了最多智慧和能量的一种工作 , 是一些独特的人在尽情倾诉 , 是以内部通用的方式说话和歌唱……每一句好诗都是使用了在吨的文学矿藏冶炼出来的精华 , 是人类不可言喻的声音和记忆 , 是收在个人口袋里的闪电 , 是压抑在胸廓里的滔天大浪 , 是连死亡都不能止息的歌哭叫喊 。 ” 此番表白干脆就是以诗论诗 , 诗如巫师的咒语无所不能 , 写诗即如朝圣远行 , 张炜就这样“依赖于诗 , 求助于诗” , 他把一生的向往和劳作交给了诗 , 以此找回丢在昨天的东西 , 获得“真正的表述的自由” 。
03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张炜的长篇小说《独药师》有题引曰:“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 可谓夫子自道 。 “那些倔强的心灵”定有一颗属于作者的诗心 。 正是凭了一颗倔强的诗心 , 张炜才会成了一个倔强诗人 。 他与自己的理想形象一体同生 , 或者相互竞逐 。 他因其诗心而敏感多悟 , 也因此而无畏无惧 。 这强大的诗心让我们想到《老子》所说“专气致柔”、“含德之厚”的赤子婴儿 , 自然也会想到张炜经常提及的童心 。 当我们把张炜看作倔强诗人的时候 , 大概也就看到了他那“绝假纯真 , 最初一念之本心” 。 张炜作为诗人的源本 , 恰是一颗未改初衷的童心 。 从张炜身上 , 总能看到天真质朴的童话气质 。 从早年的芦青河系列 , 到后来的《刺猬歌》、《你在高原》 , 他的作品皆元气充沛 , 充满雄浑勇猛的力量 , 虽深邃亦不乏机敏 , 悲悯而不乏智趣 。 他没有板着脸搞严肃 , 反而将一些精灵古怪、滑稽好玩的元素点化其中 , 一个生有怪癖的人物 , 一句挠人心窝的口头禅 , 一段旁逸斜出的闲余笔墨 , 看似无所用心 , 实则多有会意 , 就像放到虾塘里的黑鱼 , 让他的作品拥有了神奇的活力 。 比如 , 《声音》里吆喝“大刀来 , 小刀来”的二兰子 , 《一潭清水》里蟮鱼一样的孩子“瓜魔” , 《古船》中疯疯颠颠的隋不召 , 《家族》中的“革命的情种”许予明 , 《九月寓言》里的露筋、闪婆 , 《蘑菇七种》中丑陋的雄狗“宝物” , 《刺猬歌》中的黄鳞大扁、刺猬的女儿 , 《小爱物》中的见风倒和小妖怪 , 《你在高原》中的阿雅、大鸟、龟娟、古堡巨妖、煞神老母等 , 这些形象假如丢掉了天真、古怪的成分 , 上述作品大概会索然寡味 。 张炜对所写人物倾注了纯真情感 , 使其承载了一种隐性的、百毒不侵的童年精神 , 也或是他蓄意埋藏的“童话情结” 。 事实上 , 自小长在“莽野林子”的张炜 , 似乎生就了对万物生灵的“爱力” , 那片林子和林中野物让他拥有了坚贞的诗心和童心 , 童年记忆常会不知不觉地映现于笔端 , 他也具备了一种自然天成的神秘气象和浪漫精神 。
好作家大概都有一颗未被玷污、不容篡改的童心 。 不管他有多大年岁 , 无论写实还是虚构 , 总能在文字里涵养一脉真气和勇力 , 就像不计得失、举重若轻的“老顽童” , 能打也能闹 , 可以一本正经地“谈玄论道” , 也可以忘乎所以地“捣鬼惹祸” , 他的作品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由王国 。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也曾说过 , 小说家能够以孩子的独有方式直抵事物的核心 , 他要比其他人更为严肃地看待人生 , 因为他具备一种无所畏惧的孩子气 , 言人所不敢言 , 道人所不能道 。 在诺顿讲座的收场白中 , 他这样强调自己的理想状态:“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 , 也是伤感的 。 ” 其实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张炜 , 作为小说家的张炜如此倔强 , 却又如此伤感:“我的全部努力中的一大部分 , 就是为了抵御昨天的哀伤和苦痛 。 ” ——这伤感成为他行文的底色 , 为他的作品染上了沉郁的调子 。 但同时又因总有天真的神采 , 使他得以经历大绝望、大虚无 , 得以行大道、走大路 。 如此 , 我们可以把张炜叫做用诗心和童心抵御伤感的天真诗人——就像他1983年写出的“瓜魔”(《一潭清水》) , 那个神出鬼没的黑孩子 , 原来就是不老不伤的精灵 , 他和张炜形影相随 , 或者早已化入张炜的血脉精神 。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假如见过张炜本人 , 你会注意到他的眼里的稚拙之气 。 读他的作品 , 更可感受到一颗天真无邪的诗心 。 他说:“一个人的变质大概就是从忘掉少年感觉开始的 , 一切都是从那儿开了头的……” 确乎如此 , 张炜早就意识到童年、出身的重要:“童年和少年的追忆是永久的 , 并且会不同程度地奠定一生的创作基调 。 ” 所以我们看到 , 不只是后期的《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这类纯儿童题材的作品与他的童年、出生地有关 , 包括他早年的少作《狮子崖》、《槐花饼》、《钻玉米地》和其代表作《古船》乃至《你在高原》 , 都与他的童年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 并且 , 他所有作品的主要背景 , 几乎都是他曾经生活过的海边故地 。 张炜一再提起他的海边故地、丛林野物 , 这类自述性文字基本点明了作家的来路 。 张炜之所以被称为“自然之子” , 他的作品之所以充满野气、天真气 , 皆与其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 童年经验、故地情结极大地影响了张炜的心理气质 , 为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资源 , 还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孔洞 , 让他来往于昨日今朝 , 随时可见旧时景物 , 可以走向遥远和阔大 。
可见张炜是一个多么恋旧、念本 , 多么看重根性、血缘的人 , 他把那片茫茫无边的荒野当作了自己的本源 , 把走向出生之地当作了寻觅再生之路 , 把居于一隅、伸开十指抚摸这个世界当作了无声的诗篇 。 我们也可以据此进入他的文学腹地 , 切身体味那种诗意的怀念与追记 , 苍凉的伤逝和乡愁 。 张炜说他是用写作为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利 , 同时也从那里获得支持 , 因此自称“胆怯的勇士” 。 他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着自己的故地 , 实质也是用文字重建那个童话般的昨日世界 。 所以他总要抚今追昔 , 要重返故地 , 还要重返童年 , 甚至有个天真的想法:“未来人们要恢复这个地方的生态时 , 如果连一点原始的根据都没有 , 那么我的这些文字起码还能当作依据 , 并且会唤起人们改造环境的那种欲望 。 ” 这种说法和鲁迅的想要以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用小说“引起疗救的注意”很像 。 当今之世 , 要用文学改造一切的想法不免有些太过天真 。 即如艾略特所言 , 就算没有巨响 , 甚至也没有呜咽 , 昨日世界已然结束 , 怎么可能昔日重来?然而就算“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 , 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 还是有人不顾一切做着天真的梦 。
也许人类一直如此 , 一边创造历史 , 一边失去故园 , 到头来只是一味地除旧迎新 , 却不知今昔何昔 , 何所从来 。 所以人们一面跟进现代 , 坠入后现代 , 一面回望过去 , 怀念古典 。 我们向慕古人 , 古人向慕他们的古人 。 春秋之际的孔老夫子 , 不也是宣称“周监于二代 ,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吗?(《论语?八佾篇》)他驾着一辆木头车周游列国 , 宣扬周礼 , 还不是被楚狂所嘲笑 , 被郑人谓为“丧家之狗” , 甚至遭到宋人追杀?最后只能悲叹久未梦见周公 , 徒恨“凤鸟不至 , 河不出图 , 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篇》) 。 孔子致力于“克己复礼 , 天下归仁”(《论语?颜渊》) , 他要抵御的不是世人的冷嘲热讽 , 乃是整个时代大局 , 是全天下的“礼崩乐坏” 。 身为一介布衣 , 却“不识时务” , 敢与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为敌 , 这样的人是不是太过不自量力 , 太过天真?可是天真的孔子直把他的天真当成了毕生的事业 。 大概正因如此 , 他才像个孩子一样拥有一颗倔强的心 , 为了一个渺茫的梦想 , 虽处处碰壁被困绝粮仍不改其志也 。 张炜不单把孔子尊为布道者、启蒙者 , 更把他称作诗人 , 说他走过的长路便是一首长长的、写在大地上的、人类的诗 。 “一个含蓄而认真的作家 , 会像孩子一样执着地守着自己的文学……作家的心情是欢欣而沉重的 , 欢欣来自天真 , 沉重也来自天真 。 思想深入生活的底层之后 , 他的天真仍存 。 谁知道作家更像孩子还是更像老人?说是孩童 , 他们竟然可以揭示世界上最阴暗的东西;说是老人 , 他们又是那样单纯执拗 。 ” 张炜的话正揭示了诗人所应有的那种深刻的天真 , 他们世事洞明而不老于世故 , 人情练达而不死于钻营 。 也难怪他会感慨:“从许多方面看 , 从心上看 , 现在人苍老的速度远远超过古人 。 古人即便到了老年尚能保持一颗充盈鲜活的童心 , 而现代人一入庙堂或商市就变得不可观了……” 所以他才特别喜欢孔子身上的孩子气 , 喜欢他的童言无忌、孩童般的纯稚 , 怀念那一颗天真而伟大的心灵 。 从这点来看 , 张炜虽自愧为“胆怯的勇士” , 却也有其刚勇的一面 , 他记住了自己的童年 , 记住了失去的故地 , 也就记住了一个原来 , 守住了一片诗意和安宁 。 作家要面对的当然不只生存环境的恶化 , 大物大欲的疯狂泛滥 , 更要面对人心凋敝 , 灵魂无所皈依之类的大问题 。 就像两千年前孔子为匡正天道人心而奔走 , 张炜则为这个世界而写作 。 为此 , 他带月独行 , 芳心似火 。
04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张炜最终是一个要到月亮上行走的梦想家 。 他拼力创造一派旷世大言 , 着意成为一名天真诗人 , 表现在文字上除了追求崇高正义美德善行 , 渲染香花芳草浪漫诗情外 , 更有其阴柔内敛、蜃气氤氲的神秘气象 。 一般而言 , 人们习惯于把张炜归类于所谓现实主义作家 。 以《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为代表的仿宏大叙事、民间叙事似乎只有一种扑向地面的解读方式 , 张炜常常被概念化为忠于现实、热衷说教的保守派作家 。 奇怪的是 , 很少有人注意到 , 其实张炜本质上原是凌空高蹈的 , 在被定义为大地守夜人的时候 , 岂不知他正将目光投向高远莫测的天空 。 就像他在《芳心似火》收尾一句所说:“让我们仰起头 , 好好凝视这轮皎皎的月亮吧 , 它是整个天宇的芳心啊 。 ” 张炜从来不是只会低头苦思、淹没在现世尘俗中的迂夫子 , 而是一个喜欢游走山野 , 不时把想象引向星空的造梦者 , 一个不安于现状 , 专爱御风而行的天外来客 。
张炜经常提起康德的一句名言: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人敬畏 , 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 实际上 , 要想简单涵盖张炜的作品 , 完全可以搬出这句话一言以蔽之 。 一方面 , 张炜致力于探究人性人心 , 另一方面 , 则是诉求天命天道 。 所谓天道人心 , 康德的话不也正为此意?先不说张炜写出了什么主义 , 仅从其早期作品来看 , 就不难发现他从一开始便突破了死板狭隘的“现实” , 打开了多重文学视角 , 创设了一种天地交泰、万物咸亨的全息化文学维度 。 胡河清认为 , 《古船》不仅仅是一部有关具体历史风貌的写真式作品 , 而是根据一系列精心编制的文化密码建构的全息主义中国历史文化读本 。 虽然也有论者认为 , 让一个整日研读某宣言的农民承担救赎使命“构成了《古船》在精神哲学的根本失败” , 未能进入象征无限可能性的广阔“灵界” , 但是这种论调好像没有看到《古船》同时具有一个《天问》的维度 , 更没有像胡河清那样 , 看到张炜是用“古船”、“地底的芦青河”、“洼狸镇”以及隋、李家族等既有独立隐喻意义又相互关联构成玄秘神话系统的文化符号 , “编制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历史未来走势的文化学密码” 。 张炜向来就是一位多藏“密码”的作家 , 看不到他的“密码” , 当然也就看不到他的另一面 , 更看不清他的“假意或真心”——“虔诚的灵魂” 。
张炜说 , 他曾偏执地认为 , 一个作家的才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上 。 对此 , 他曾自嘲说这有些可笑 。 但是 , 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融入“自然” , 真的能够领会道法自然 , 大概就不会觉得张炜偏执可笑 。 张炜在某种程度上把诗人(最优秀的作家)当成了具有出奇感悟力的特殊生命——他们能够“特别敏感地领会自然界的暗示和启迪” 。 诗人“站立在什么土地上、呼吸着什么空气、四周的辞色和气味 , 这对他可太重要了 。 他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 血脉相通 。 他是它们的代言人 , 是它们的一个器官 。 通过这个器官 , 人类将听到很多至关重要的信息 , 听到一个最古老又最新鲜的话题 , 听到这个星球上神秘的声音” 。 张炜所说的自然/世界显然不仅是视觉上意义上的风景物象 , 诗人也不是仅会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嘴子客” 。 在他看来 , 独立、绝对强大的“大自然”拥有深不可测的无穷秘密 , 包蕴了许多用科学、理性难以言说的神异信息 , 而诗人就像能够施行天人感应的“神巫”一样 , 可以为天地代言 , 发出通达“神明”的声音 。 张炜好像深得中国本土“神传”文化之真味 , 又如同一名崇信个体直觉的超验主义者 , 对他来说宇宙自然绝非无知无觉的物质集合 , 而是一个承载无限生机、含藏永恒“神性”的未知世界:“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 它在对我们的全体实施一次抽样检查 。 ” “生命中有一部分神秘力量 , 它很早就决定了这个生命的道路和走向 。 ” 鉴于这种认识 , 他才把诗人/作家看成了身有异能的通灵者 , 几乎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玄妙已极的特异功能 。

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张炜引论// //
可是 , 那种神奇的“冲动和暴发”说起来容易 , 做起来何其难矣!所以张炜又说 , 由于物质主义的盛行 , 一种无所不在的萎靡只会把人的精神向下导引 , 进入尘埃 。 “人没有能力向上仰望星空 , 没有能力与宇宙间的那种响亮久远的声音对话 。 每当人心中的炉火渐渐熄灭之时 , 就是无比寒冷的精神冬季来临之日 。 ” 具有这种对话能力的 , 很可能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了 。 这样的人“整整一生都对大自然保留了一种新鲜强烈的感觉” , 因此才能见人所未见 , 感人所未感 , 从而“跟植物 , 跟自然界当中看得到的所有东西对话和‘潜对话’” , 进而获得一种特异的感受——“这种感受好像与神性接通了” 。 那么 , 究竟何为“神性”?张炜的解释是:“神性就是宇宙性 。 神性和宇宙性越来越少 , 那是人类缺少了对头顶这片天空的敬畏……伟大作品应该有神性 , 它跟那种冥冥中的东西、跟遥远的星空有牵连 , 一根若有若无的线将它们连在一起 。 ” “神性是一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大自然背后甚至茫茫宇宙里的那种‘具有灵魂’的超验力量 , 它可能接通深藏在人类身体里的想象力 , 并且激发出永恒的渴望——宗教感就这样产生 。 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写出这种‘神性’ , 就是使得自身突破了生物性的局限 , 进而与万物的呼吸、大自然的脉搏 , 与宇宙之心发生共振或同构 。 ” 这样看来张炜好像在宣传“迷信” , 他把文学说得“神神道道” , 把写作说得玄而又玄 , 是不是表明他坠入了一个“泛神论”的怪圈?或者只是策略性地祭出了一面“神性”的大旗?当然 , 究竟有“神”无“神” , 究竟“神性”何在 , 一切都有作品为证 , 这里姑且设一悬念 , 留待详加讨论 。 不过这里仍可略述他的主张:“神性不是让人更多地去写宗教 , 不是让人鹦鹉学舌地去模仿无尽的仪式 , 而只是唤回那颗朴实的敬畏的心 。 ” ——可见张炜并未把自己等同于“迷信”者或宗教人士 。 与“神性”、“宇宙性”的亲和对他而言纯属一种自小形成的生命本能 。 他在海滩丛林长大 , 那样的生活环境是向整个宇宙完全敞开的 , “抬头就是大海星空 , 想不考虑永恒都不可能” 。 中年时他还在一篇散文中说:“直到今天 , 还能兴致勃勃地领略天上的星光 。 ” 可以说 , 少年时的星光如同神秘的种子 , 被张炜装进了背囊 , 也种到了心里 。 借了这星光 , 他独自去游荡 。 靠了这星光 , 他找到了自己的“神” 。 所以 , 我们经常会在他的作品里看到“微弱的星光”(《木头车》)、“一天星光”(《山水情结》) 。 在早期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中 , 张炜就曾十分抒情地写道:
天空被忽略了:多少明亮的星星!多少上帝的眼睛!天空没有乌云 , 苍穹的颜色却不是蓝色的 , 也不是黑色的;这时候的天空最难判定颜色 , 它有点紫 , 也有点蓝 , 当然也有点黑 。 白天的天空被说成是蓝蓝的 , 其实它多少有点绿、有点灰 。 真正的蓝天只有在月光的夜晚!皎洁的月光驱赶了一切芜杂、一切似是而非的东西 , 只让苍穹保持了它可爱的蓝色!哦哦 , 星光闪烁 , 多明净的天幕啊 , 多么让人沉思遐想的夜晚啊!
这样对天空的精确描写显然来自作者本人的真切感受 。 不仅如此 , 他的作品里还会经常出现仰望星空的人 , 这个细节的来源显然也是张炜自己 。 他说:“我相信一个作家虽然什么都可以写 , 但他总会让人透过文字的栅栏倾听到一个坚定的声音 , 总会挂记着苍穹中遥远缥缈的星光 。 ” 这星光几乎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精神意象 , 也为张炜的作品洒上了从天而降的神圣的微光 。
“在月亮上行走过的人 , 给他个县长还干吗?”张炜就是从月亮走来的人 , 他干的事必定要比“县长”大得多啊!“每一个时代的精灵 , 往往都会自觉地捕捉那些真正无私和宽容的人 , 让他‘神魂附体’ 。 ” 想来张炜的写作大概也是一种“神魂附体”吧?张炜还说过:“一个人总应该有自己的‘神’ , 没有这个‘神’ , 人与人之间就没法区分 , 总会是一种色调 , 即千篇一律 。 每一个人使自己区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事物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 就是守住自己身上的‘神’ 。 ” 所谓自己的“神” , 虽只是一个比喻性说法 , 但也说明了自我拣选、自我持守的重要 。 我相信张炜一直守着自己的“神” , 否则又怎么可能在他的作品里召唤“神性” , 呼告永恒?
因了对于诗性的追求 , “文学通向了诗与真 , 如同寻找信仰” 。 在张炜看来 , 在这片大多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 , 一个写作者有了类似的写的志向 , 差不多也就等同于“为了荣耀上帝”而写作了 。 张炜一再表示 , 文学只能是神圣的 , 对他来说 , 写作就是一场漫长的言说 , 是灵魂与世界的对话 。 这样的写作必然危险 , 必然要依赖信仰 , 需要强大的勇力 。 那么 , 如何才能保持一种“真勇” , 如何才能守住“特别的诗人的灵魂”?张炜曾借用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念来解释当今世界的阴阳失衡——如果物质是阳性的 , 精神就是阴性的 。 在“大物”居上的阳性时期 , “阴”就会受到损害 。 相对于物质的显性 , 精神活动则是隐性的 , 也即阴性的 , 所以一切精神活动都在无形中进行 , 在默默无察的环境里滋生蔓延 。 “巨大的阳性社会一定会投下浓重的阴影 , 那里成了诗人的立足之地” , “为了躲避强烈逼人的阳性 , 诗人只好留在了‘阴郁’的空间里” 。 这个“阴郁的空间”对诗人至关重要 , 因为诗就像生命里的一种有益菌 , 只有在阴郁处才能繁殖、生长 。 张炜说 , 只有人文精神才能平衡一个倾斜的世界 , 而“诗”正是“滋阴潜阳”的大补之物 。 所以他才指出:“现在的诗以及所有的诗性写作 , 也包括极少一部分小说家 , 算是遇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们生存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跟整个阳性的社会脱节、隔离 , 以至于部分地绝缘 , 于是反而成为一个极好的屏障和境遇 。 如果把他们拉到现世的阳光下照耀以至暴晒 , 他们正在阴湿中的烂漫生长不仅马上停止 , 而且会很快凋谢和枯死 。 ”因此 , “诗人只有待在阴郁的空间 , 在这里悄悄地、放肆地生长” 。 张炜为中国诗人指出了一种中国式的生存之道 , 这也透露出一种以退为守 , 以守为攻的隐逸倾向 。 张炜就是这样一位从显性世界回到隐形世界的孤独梦想家 。 我们不得不说 , 这位天真诗人正是从非诗的阴影里走向了诗 , 在“渎神”的背景里找到了自己的“神” 。
张炜55岁那年说过一段话:“一个纯文学作家 , 最好的创作年华是四十五岁到六十五岁这二十年 。 在这个时候 , 生活阅历、艺术技能 , 还有身体 , 都是比较谐配的 , 是一个契合时期 。 三十而立 , 四十不惑 , 五十知天命 。 知了天命才能写出有神性 , 有宇宙感的作品 。 天命就是神性、宇宙性 , 所以五十岁之后往往才能写出真正的杰作 。 ” 孔子曰:“不知命 , 无以为君子也 。 ”(《论语?尧曰》)张炜显然是以心到“神”知的方式上承天命的 。 如果按其所说 , 他正是在最好的创作年华 , 写出了大批耀眼的作品 。
可以说 , 除《古船》、《九月寓言》之外 , 张炜其他重要作品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 虽不好说每一部都是杰作 , 但是应该说每一部都是诗人的梦想之书、天命之书 。 张炜用他不竭的诗心和童心 , 写下了无声的大言 , 伟大的沉默之诗 。
张炜50岁那年 , 曾在英国的一个诗歌节上发了一句豪言:“到六十岁以后 , 我要成为一个大诗人——能成则成 , 不能成硬成 。 ” 张炜14岁学诗 , 奄忽已至半生矣 。 然其总是愧称“诗人” , 概因对诗期之太高 , 对己苛之太严 , 他矢志以求的诗 , 原本和天上北斗一样 , 它确实就那儿 , 又似乎遥不可及 。 然而诗人 , 不就是要指向一个遥远 , 奔向一个未知么?现在张炜又准备了很多精美的本子 , 他说 , 要用最好的本子 , 写出最好的诗 。 如此 , 张炜成诗 , 正当其时 。
本文节录自《张炜论》引论部分 。 首发于《中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 《新华文摘》2019年第11期转载 。
- 齐白石画山水:懂的人不多,骂的人却不少
- 一个人的长征:追寻孙子
- 晋朝电视剧为何只拍到司马炎登基统一三国,以后的事情为何不拍?
- 《圣斗士星矢》重病的伊利亚斯为什么还能对冥斗士产生重大威胁?
- 凿壁偷光的匡衡,后来怎样了?成了贪官为害一方
- 古代最有钱的县城大街,位于山西,现为世界遗产!
- 小脚的起源:为防疫古人如何解决大妈们串门、扎堆的问题
- 元宵节的由来与传说
- 自编教材评审的标准是什么
- 曹操有14个老婆,12个是抢来的寡妇,一代枭雄为何爱抢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