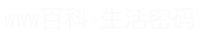我与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我与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来源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 | 王宏昌

我与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骑兵宣告下马 。 从此 , 我国除边防哨卡等特殊部位留有少量军马外 , 骑兵这个兵种已成为过去的辉煌 。 那么 , 骑兵这个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建立过卓著功勋的兵种 , 其生活和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又是怎样退出共和国军事舞台的?笔者作为最后的骑兵部队中的一名老兵 , 亲历了骑兵下马的前前后后 。
离地三尺的空军
1973年10月 , 我们一行百余名陕南青年被批准入伍 , 跟着接兵的军队干部登上了西去的闷罐子列车 。 一路上我们见来往的新兵、老兵很多 , 却唯独我们的军裤显得很特殊:上面粗大呈兜状 , 下面细窄紧口 , 钉有三只扣子 。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骑兵专用的马裤 。
那时候 , 我们一帮陕南娃从小连马都没见过 , 更别说骑马了 。 因为对这种军裤感到很新奇 , 我们就缠着接兵干部问:“我们的部队是啥兵种?”
接兵干部起先不肯说 , 被我们问得紧了才说:“是空军 , 离地三尺的空军!”
我们受“空军”二字的鼓舞 , 漫漫河西路上激动得难以成眠 。 当然 , 一到部队营地,我们才知道是离地三尺的“马背空军” 。
两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后 , 我被分配到新疆军区独立骑兵营二连五班当战士 , 不久被调任连文书 。 我们连对外称疆字215部队62分队 , 驻地在奇台县水磨河畔 , 被老百姓亲切称为“钢铁二连” 。 由于是畜力化的骑兵部队 , 营连排班的基数都很大:一个连队有4个排 , 每排有3个班;每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 , 战术训练时由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各带一个小组 , 呈前三角或后三角队型战斗编组 。 这种编组在当时的战术、战略形势下易守善攻 ,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 每个人配军马一匹 , 另外每班还配有备用马一匹 。
所配军马来自两个地域:一是内蒙古军马场的蒙古马 。 这蒙古马体小但很机灵 , 侦察、夜袭、突围是它的强项;二是新疆伊犁军马场的新疆马 。 这种军马高大魁梧 , 胸肌发达 , 四肢修长 , 是急行军、乘马斩劈打冲锋的强将 。 伊犁军马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急如流星 , 但常常对骑手的裆部造成危害 , 因为实在颠得厉害 , 只有冲锋飞奔起来才能平稳;而蒙古马轻巧灵活 , 走起来很平稳 , 与伊犁马正好是一柔一刚 。
因此,骑兵部队给战士配备军马时有讲究:给军事干部、战斗班排配备伊犁军马;给部队后勤部门如卫生所、炊事班及连队的司号员、卫生员等则配备蒙古军马 。
于是战士们把伊犁马称为“老伙计” , 而把蒙古马称为“蒙古蛋子” 。
酸甜苦辣的生活和训练
骑兵生活是极为清苦、繁忙和单调的 。 骑兵的起床时间要比步兵早半个小时 。 早晨起床号一响就集合出操 , 出完操还不能像步兵那样回宿舍洗涮 , 要从操场直接扑进马厩 , 用扫把和拖把 , 把一晚上积累的马粪清理出去 , 以班为单位 , 各班互相拼速度、拼干劲 。
而这时 , 值夜班喂马的战士则挎着斗 , 把料和食盐撒进每个马槽 , 让吃了一夜草的军马换个口味 。 我们收拾完马厩 , 就得赶往宿舍洗脸 , 稍慢一步 , 开饭的号就响了 。
列队唱歌进了连队食堂饭厅 , 各张桌子上已打好了咸菜和素炒洋芋片 , 玉米糊糊在大盆里 , 小馒头在笼里 , 自己拿 。 这一刻什么都顾不得了 , 人人都扑上前去 , 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 。 不这样不行 , 因为吃过早饭就要扑进马厩 , 把军马牵到外面的大棚下 , 把马头高吊在铁链子上――助军马消化 , 行话叫“吊马” 。
如果哪位战士天天早晨落在后面 , 你就是落后分子 , 周末班务会上就不太光彩了 。
然而不论新兵怎么努力 , 总是落在老兵后面 。 原来新兵吃得多、吃得慢 , 而老兵们为了传帮带新兵 , 使了手段――一进食堂 , 吸溜喝下一碗汤 , 抓过两个馒头夹上咸菜 , 边吃边往马棚去吊马 。 老兵每人四匹马牵出去吊上了 , 新兵这边第二个馒头还没吃完呢 。
如此三番搞得新兵们吃不饱早饭 , 到中午就往饱里吃 , 大约50克一个的小馒头 , 伸出左臂来把馒头从手腕处排到肩膀上 , 不下10个吧 , 能一口气全吃完 。
这样长时间下去 , 到新兵当了老兵 , 这胃病也就落下了 。
吃过早饭 , 以排为单位各派出一人去替换喂马、看马的 , 派出一人去换哨 , 再派几名去割草或跟了马车去县粮食局购马料 , 剩下的人就是训练了 。
骑兵训练分马术训练和步兵训练两大内容 , 中午和下午的正课时间一般被用来训练骑兵战术 。 号声一响 , 我们要像出膛的子弹那样一头扎进马厩备好鞍 , 然后牵马到操场上听指挥员的号令 。 先是上马下马 , 继而是立正稍息 , 口令和步兵的一样 。 区别是余音拉得长一些 , 以便使军马在骑手的操纵下反应过来 , 做出规范的立正、稍息或卧倒之类的动作 。
骑术训练的第一课最为艰难 。 一班战士由班长、副班长带着 , 十几骑成纵队到戈壁滩上的雪地上走一大圈 , 踩出一个跑马场 , 然后一个新兵后面跟一个老兵 , 班长站里圈 , 副班长站外圈 , 要求新兵们把马镫搭起来 , 两脚悬空 , 手里只抓软兮兮的缰绳 , 不许抱马鞍 , 不许抓马鬃 , 脚下又无镫可踩 。 这样慢步走还平稳一些 , 心里咚咚跳着也罢了 , 问题是班长突然改变口令 , 拉长音喊“快走――” , 老兵们从后面一鞭子 , 马就小跑起来 , 只见新兵们左摇右摆的 , 几下就一个个地从马背上栽进雪窝里 , 如下饺子一般 。 掉下来还得再爬上去 , 自己不爬就让老兵把你弄上去 , 不然鞭子伺候――训练场如战场 , 谁可怜你!
这种不让踩镫的骑法 , 连老兵也受不了 , 更何况我们这些从小连马都没见过的陕南娃呢!几天下来 , 有的战士的裤裆里都磨坏了 , 只好用纱布缠住 。 晚上坐床上 , 身边放一碗水 , 用手抓水敷在裆里 , 一层层轻轻地往下揭被血凝固的纱布……
晚上值班喂马也不轻松 , 前半夜还好些 , 轮到下半夜人太困乏 ,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在草窝里睡过去 , 睡过去就有军马可能卧下来 , 次日天明及至发现 , 这匹马轻则结肠 , 重则死亡 , 那么值班战士就轻而易举地背上一个处分 。
这并非耸人听闻 。 要知道 , 一匹马从入伍到退役 , 是建有和战士一样的档案的 。 那时候全国性的穷日子穷着过 , 一个战士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0.65元 , 实际开支中要求每天节余0.05元 , 就是说一日三餐包括节日加餐 , 实际每人每天开支只能控制在0.5―0.6元之间 , 而每匹军马一天的生活费是1.75元 , 吃多少草、多少料、多少盐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
因此骑兵部队就有“两套班子” , 即营里有一名专管军马生活的副营长、参谋和助理员 , 还有一个军马卫生所;连里有军马生活管理员(称马干上士)和钉掌工、军马卫生员 , 这些机构设置与战士的后勤生活机构正好是两套班子 , 而且军马的“班子”更牛气 。
因为一旦行军 , 军马就成了我们的“无言战友” , 所以我们对军马的“多吃多占”毫无怨言 , 只有精心伺候它们了 。
拍摄电影的经历
1974年 , 邓小平重返中央军委 , 部队生活又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
真是没想到啊 , 几部涉及重大军事题材和军旅生活的影片开拍 , 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制组进驻我们连 , 由我们承担协拍骑兵在战场上发起冲锋的光荣使命 。
于是我们有了拍摄电影的特殊经历 。
我们带着几卡车服装、道具 , 骑着自己心爱的军马 , 浩浩荡荡来到博格达山脉的哈熊沟 。 我们按照平时的训练序列 , 以野战方式搭锅造饭、乘马骑射训练 。
那时不像现在排戏 , 只顾吸引眼球 , 而是一切都要服从实战实况要求,最后才在摄制人员的指导下 , 演练几个应景动作 。 摄制组要从我们中间抽调一部分人化装成敌军 , 可我们谁也不愿当敌人 , 最后只好由指导员点名 , 才确定了穿敌军衣服的人选 。
我们换上战争年代敌我双方的服装 , 准备好烟火等一应道具 , 等导演一声令下 , 我们就在连长的带领下 , 从山头高举战刀向下冲锋 。 一时间炮声四起、浓烟滚滚、杀声震天 , 仿佛真的置身在激烈交锋的战场上……
一连十几天 , 我们按照摄制组的要求 , 重复着那几个反攻、冲锋场面与动作 , 终于完成了协拍任务 。 遗憾的是,在以后多年里 , 不论眼睛睁多大 , 我们也从来没在电影里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
倒是装成敌人的战友中 , 有人在一部影片中偶而露过面――那是在我军的追击下 , 敌人从马上掉下来 , 被我骑兵战士挥起战刀砍杀时惊恐不堪的镜头 。
虽是“昙花一现” , 可我们还是被这难得的镜头乐得屁颠屁颠的 。
野营拉练的情趣
那时候 , 骑兵部队的拉练在乌鲁木齐以东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东三县是一道风景 , 也是三县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共同怀念的事情 。
当时的情况是 , 国民经济很不景气 , 物资贫乏已到了难以尽述的地步 。 部队也不例外 , 那点可怜的军马伙食费根本买不来应消化的标准 。 没办法 , 只好每年的四月份 , 请几名哈萨克族牧工 , 带上我们几个战士 , 把全部的军马赶到南山牧场去集体游牧 。
全连战士没了军马 , 就发挥拥有很多马粪的优势 , 开荒种草、种料、种菜 。 秋后草料收了 , 就赶紧把马赶回来 , 抓紧时间训练战术、马术 , 把荒废几个月的军事技能捡起来 。
军马的饲草 , 主要是奇台和木垒、吉木萨尔三县老百姓在留足队里牲口饲草的前提下 , 以“支前拥军”的形式 , 用马车给部队送来的 , 叫“军草” 。 这些生产队送饲草都是有任务的 , 公社、县上要检查、评比的 。 尽管数量有限 , 部队还是十分感激 , 酒饭招待送草群众 , 饲草照价付款 。
临走时 , 再派几名战士给老乡装满满一马车马粪拉回去 。 部队知道 , 这样做生产队就多了份肥料;再者 , 也能使送草社员多挣几个工分 , 有利于调动送军草的积极性 。
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 , 生产队的军草也是有限的 。 每到农历11月初 , 部队的军草垛眼看剩底 , 细细一算 , 要熬过春节前那几个月 , 就得赶紧率部外出野营拉练 , 顺便给军马混口“饭”吃 。
于是 , 冬、腊两个月的野营拉练就开始了 。 选点一般选在无送军草任务的偏远乡村 , 或者那些拥军模范村 。
我们当年所走过的路线是:第一站 , 奇台县西地镇桥子村;稍事休整后赶到回民庄子旱台子村;再下面是木垒县的新户、东城、西吉尔、英格堡;奇台县的平先、麻沟梁、吉布库、东湾、老鸦庄子、白杨河;后经吉木萨尔县的泉子街等地返回 。 偶然也对路线稍做调整 , 但大致如此 , 每个点3―5天不等 。
要说那时的军民关系 , 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 每到一处 , 群众就为我们烧好了热炕 , 准备好了草料 , 收拾好了棚圈 。 而我们每每赶到 , 一下马就帮老乡挑水、清理积雪、挖柴火等;遇到队里冬天搞水利 , 我们也参与其间 , 弄来炸药开山修渠 , 这比老乡烧麦秸化冻挖渠可快多了 。 住下后帮着训练民兵 , 与党团支部一起联欢 , 用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给老乡们演出 , 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 亲如一家 。
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 , 我们那时野营拉练一般是以班为伙食单位 , 一个班住到一户老乡家 。 我们白天出去帮老百姓干活 , 而老百姓就铡了自家的草喂我们的军马 。 我们的战士做饭笨手笨脚 , 房东大妈、大嫂就做好拉条子、揪片子端到面前 , 起初我们怕违反纪律 , 坚持不吃 。 后来首长见这成盆的饭剩着也不是个事 , 就下命令说“先吃了再说” 。 我们这些吃惯了糊糊、馍馍的大兵一下子吃到这么可口的家常饭 , 简直把生日年节都忘了呢!
临分手时 , 军队和老百姓恋恋不舍 , 眼睛潮乎乎的――如今想来这的确是极真诚的 。 我们把吃了饭的钱执意留下 , 但是被房东再三推辞 , 推到情急之下 , 房东变了脸:要给钱你们明年别来了 , 到饭馆里吃去!
于是我们默默无言 , 只好悄悄地把我们随身带的大米、清油留给房东――要知道 , 那时当地老百姓想弄到一斤大米是很困难的 , 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凭粮本每月才能买到一斤米、半斤油 。
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下来 , 我们的军马度过了饥荒 , 然而老百姓的牲畜却常常要到野外去啃草根度命 。 我们虽然照价补偿了草料费 , 然而在那个年代区区几个钱又能派什么用场呢?那份真诚、那份情义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呀!于是,在全国仅有的骑兵奉命全部下马的1975年 , 军区在讨论退伍后的军马向何处去时 , 部队党委首先想到的是奇台、木垒、吉木萨尔三县的老百姓 , 无任何代价地捐献给三县人民支援农业生产 。
1976年 , 我们下马后的原骑兵营与驻守北塔山的边防独立步兵第十营合编 , 与从石河子调防过来的步九团机关合并成“新疆军区边防第二团” , 依然驻防边陲 。
于是,这支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 走完了她历史的最后一站 , 这个古老而又辉煌的兵种永远告别了当代军事序列 。 (摘自《新疆日报》)

我与共和国最后的骑兵部队// //
诚邀有志之士投稿 ,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 邮箱:107000701@qq.com
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 仅供参考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 古代最有钱的县城大街,位于山西,现为世界遗产!
- 评职称课题最后一名有用吗
- 柴进复辟梦想的破灭:梁山好汉中人品的佼佼者,也是下场最好的
- 别不信,最早把牡丹叫“国花”竟然是她!
- 陈子昂最孤独的诗,开篇就是千古名句,可谓时势造英雄,光照中华
- 电动车最大的能耗杀手是什么?小鹏G3的能耗表现到底如何?
- 古代墓地风水十不向秘诀,墓地最佳风水坐向及朝向的吉凶
- 浪子燕青:《水浒传》中素质最全面的一位好汉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
- 洞口用铁笼子伪装!萨达姆最后的藏身之地,每次仅能进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