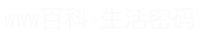父亲的党内诤友:多少往事烟雨中[16]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父亲的党内诤友:多少往事烟雨中[16]
本文为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往事的长篇回忆之十六 。 陈占祥为建筑师梁思成的合作伙伴和好友 , 于1950年一起推出老北京城的改造规划方案《陈梁方案》 , 本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秘辛 , 或可一读 。
原载于《当代》2009年第2、3期 , 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父亲的党内诤友:多少往事烟雨中[16]](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0207/3766c1f8ecbd468091e7f21e81f2cb39.jpeg)
父亲的党内诤友:多少往事烟雨中[16]// //
前文链接
(点击蓝色标题可前往阅读)
乘鹤远去程应铨:多少往事烟雨中[15]
“右派”父亲的党内诤友(本章有删节)
李正冠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 。 这个与父亲命运息息相关的名字多少次在我耳边响起 , 我像熟悉自己家人那样熟悉他 , 却一次也不曾见到过他 。
听父亲说 , 和多少热血男儿一样 , 李正冠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冲出书斋 , 投入抗日洪流 , 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干部 。 在建筑设计院担任党委书记的李正冠 , 儒雅斯文 , 一身书卷气 , 这使他成为建筑设计院许多知识分子的朋友 。
父亲从沙岭劳改回家后 , 不知设计院会如何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 内心不免忐忑 。 若继续做建筑设计 , 那会遇到很多麻烦 。 “右派”虽然摘帽 , 也永远低人一等 。 而建筑设计又极富个性和创意 , 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 , 很难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劳动 。
“在夹缝中求生存 , 整天夹着尾巴搞设计 , 等于穿着小鞋走山路 , 还不如在大山里种树 。 ”父亲对尚不可知的未来岁月 , 很是心灰意懒 。 当时我正在女附中读初三 , 面临升高中的考试 。 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 , 说北京师大二附中正在办一个文科实验班 , 要从师大的三所附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入 。 经挑选合格的学生 , 可以免试保送入学 。 我回家和父母商量 , 是否要进二附中读书 。
“这种事 , 父母的意见仅供参考 , 因为在这条路上走的是你自己 , 谁也取代不了 。 ”父亲说 , “不过 , 你学文科 , 我这个爸爸会带给你很多麻烦 , 爸爸要事先告诉你 。 我欠孩子们的债 , 举一生之力也偿不清 。 但我感激你们 , 你们让我骄傲 。 ”
我还是决定上二附中 。 父亲嘱咐我说:“全班同学都要参加升高中的统考 , 人家在考场上拼得汗流浃背 , 你一身轻松 , 袖手旁观 , 就不够厚道了 。 为大家做点事吧?”
母亲给了我三块钱 , “不是连考两天吗?每天在教室门口放一大脸盆洗干净的西红柿 , 给同学们解解暑 。 ”
我觉得母亲真聪明 。 父亲又叮咛说:“把东西放下就走 , 千万别吵得唯恐天下不知 , 那还不如不做 。 ”
我照父母说的去做了 。 两天考试完毕之后 , 连我住校使用了三年的脸盆也没敢拿回来 。 四十多年后 , 女附中的同学们聚会 , 还提起考试时教室门口的西红柿 , 不知是谁放的 。 我仍什么也没说 , 却想起了已双双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母 。
周六晚上 , 父亲下班时 , 望着刚刚摆好的餐桌问母亲:“还有酒吗?”
“只有半瓶金奖白兰地 。 ”母亲连忙找出酒瓶和杯子 , “什么事值得喝酒?”
“算是好事啊 。 ”父亲边斟酒边说 , “今天 , 李正冠找我谈话了 。 ”
“又直呼人家名字 。 ”母亲把一双筷子递到他手里 , 埋怨道 , “人家是设计院和规划院两院的书记 , 谁都李书记长李书记短的 , 哪有人像你这样?哪个当官的听你这么叫他会心里舒服!”
“口口声声把人家官衔挂在嘴上 , 我心里还不舒服呢 。 ”父亲啜了一口酒 , 笑道 , “等于一张口脸上就写着:我是马屁精 。 ”
“好好 , 快说李书记跟你谈什么了?”母亲忙着为大家布菜 , 父亲第一 , 孩子们其次 , 母亲自己永远是最后 。
原来 , 李正冠为了发挥陈占祥和华揽洪的一技之长 , 专门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室” , 让两位“摘帽右派”做建筑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翻译工作 。 华揽洪法文胜于中文 , 陈占祥英文长于中文 。 经历了砂岭几年的劳改生活 , 对于父亲来说 , 这已是很理想的归宿了 。
20世纪60年代初 , 中国人对国门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 提起西方世界和港台 , 总是一副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于水火的悲天悯人情怀 。 我在学校表演过一个配乐朗诵 , 描述一个名叫杰克的十一岁美国黑人孩子 , 为挣钱养家 , 背着牙膏广告牌子在大街上游走 , 受尽欺凌的悲惨故事 。 还有一首诗叫《爸爸要出卖眼睛》 , 讲的是西班牙一位父亲 , 因为养不起四个儿女 , 决定出卖眼睛 。 朗读这些诗歌时 , 我和台下的同学们都泪流不止 。 我们心中的世界 , 中国是中心 , 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受着地主资本家的剥削 , 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眼中的外部世界 。
由于父亲是英国皇家建筑规划学会会员 , 终身享受英国《建筑评论》杂志的免费赠阅 。 父亲觉得奇怪极了 , 无论我们搬到哪里 , 这份杂志永远准确无误地送到我家 。 这本比十六开本还大 , 像一厚本书似的杂志 , 刊登着英国和世界建筑界、规划界最新的建筑技术、建筑理论方面的信息和文章 。 他成了父亲遥看另一个星空的“天文望远镜” 。
李正冠对父亲说:“中国人手里很难找到第二本这种杂志 , 你能不能把它每期关于技术和理论方面的文章 , 都翻译成中文 , 成为我们北京建筑设计院资料室的库存资料?”
父亲喜出望外 , 说:“我能不能把杂志都运到资料室来?我家的杂志堆成山了 , 没地方放 , 我担心老婆哪天当废纸卖了 。 ”
李正冠连连摆手说:“卖不得卖不得 。 你以后把每期杂志都拿到办公室来吧 , 将每期内容的精华 , 都翻译成中文 , 这就是你的工作 。 不过 , 这些文章译好了要存档 , 不可以随便让人看的 , 不然麻烦大了 。 ”
几天后 , 设计院来了一辆平板三轮 , 一捆一捆的英文《建筑评论》杂志 , 摞得像小山一样高 , 全都运走了 。 就这样 , 有着皇家规划学会会员头衔的父亲 , 成了建筑设计院一名英文翻译 。
“跟在蛟河县城煤铺里的顾宪成比 , 你应该是万幸了 。 ”母亲常这样安慰父亲 。 父亲就摇头叹息道:“宪成一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 。 ”
李正冠隔三差五来看父亲和华揽洪翻译的文章 。 有些弄不懂的地方 , 还要求父亲详细讲解 。 天长日久 , 他对这些杂志上的文章越来越有兴趣了 , 每周都要到父亲的办公室来几次 。 一次 , 他对父亲说:“我有一个计划 , 想向你和华揽洪学英文和法文 , 每周英文、法文各一节 , 如何?”
父亲很高兴地回答:“当然好 。 领导如果都肯学习 , 是苍生之福啊!”
李正冠说:“万事万物要有参照和比较 , 不然就坐井观天 。 知己知彼 , 百战不殆 。 我们不知彼 , 怎能知己?连自己站在哪条起跑线上都搞不清楚 , 还能不盲目吗?”
父亲说:“那你就一定能学好 。 学习是为了更接近客观真理 。 不尊重科学 , 一切想当然 , 最后受惩罚的是自己 。 ”
每周各一节英文、法文课 , 成了李正冠雷打不动的日程 , 北京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成了中国建筑界两大“右派分子”的学生 。 父亲说 , 每到上课时 , 父亲走进李正冠的办公室 , 他总是站起来 , 笑说:“欢迎陈先生光临 。 ”下课时永远会把父亲送到门口 , 像小学生一样说:“谢谢先生 , 再见 。 ”但平时在设计院的员工面前 , 他只称父亲为“老陈” 。 父亲说:“在右派根本不被当人待的年代 , 李正冠能做到这样 , 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 ”
每周的英语课之后 , 他也会和父亲谈许多其他的话题 。 他曾告诉父亲 , 自己在“七七事变”后离开就读的河北师范 , 与不愿在敌占区做亡国奴的学生们一路徒步南下 。 那时 , 他结识了一大批北京师范大学的流亡学生 , 共同向尚未被占领的山东境内进发 。 在那些学生中 , 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 , 自己也从此走向了革命 。 但他一生心系校园 , 心系读书岁月 。 李正冠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 对学习的认真刻苦 , 父亲每每提起都会说:“如果党的干部都有如此强烈的向学之志、求知之心 , 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 ”
李正冠也问及父亲被专案组追查到天涯海角的“历史问题” , 如“海员俱乐部”、“罗斯福夫人接见”、“世界青联大会副主席”等等 , 父亲一一告之 。 李正冠听得极其认真 , 还不时提出许多询问 , 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 。 很多时候 , 他只是默默地聆听 , 不置一词 , 不加一句评论 。 只是当父亲讲到他为素不相识的中国海员权益而奔走呼吁时 , 李正冠的眼睛湿润了 , 父亲忙低下头 。 李正冠急急背过脸 , 站起身 , 踱步面向窗口 。 伫立良久 ,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 , 转身回到桌边 , 仍是什么也没说 , 什么也不解释 , 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 他什么也没听到过 。
父亲说 , 他每次给李正冠留的作业 , 他都完成得非常认真 。 父亲有时要求他翻译一篇建筑方面的短文 , 英译中往往很顺畅 , 中译英则会出现很多“中国式”的英文 。
“这需要语言环境 。 ”父亲安慰他说 , “你没在那样的语言环境下生活过 , 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该用哪个词 。 ”
“有没有可以弥补的办法?”他问 。
父亲想了想说:“多读原文版的小说 , 多看原文版的电影 。 很多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 , 即使在国内英语很流利 , 但到了外面还是发傻 。 这就好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发音 , 和普通北京市民的说话发音差别很大 。 最好一遍一遍地读书 , 反复地看片子 。 写文章的人读书破万卷 , 下笔如有神 。 学语言也一样 , 读书破万卷 , 出口能成章 。 ”
那个年代 , 电视机没有普及 , 更没有什么录像机 , 反复看原版电影是不可能的 。 多读英文原版书不成问题 , 父亲的书架上就有很多 。 后来 , 父亲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家里拿一本英文书借给李正冠 , 李正冠就真如蚂蚁啃骨头一样把这些书读了下来 。 父亲常对我们说 , 你们真该向李正冠学习 , 他学习知识的狠劲儿 , 简直就像在枪林弹雨里冲锋的敢死队 , “尤其是你们俩 。 ”父亲指指我和妹妹说 , “你们要是肯下李正冠那样的苦工夫 , 肯定如虎添翼呀!”
我摆着手大笑说:“那可不行 。 我们要是成了老虎 , 兔子们可怎么活呀!”
“我可不当母老虎!”妹妹笑着大叫 。
随着李正冠英文水平的提高 , 他与父亲之间更加相互了解亦日甚 。 每次上完课 , 他们会在一起聊聊天 , 偶尔步行去不远处一家“礼士路餐厅”吃饭 。 父亲说 , 他每次都走在李正冠身后 , 和他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 虽然他们从没为此约定过什么 , 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
李正冠对建筑理论问题表现出很强烈的关注 。 他认为 , 要提高中国建筑界的总体水平 , 必须先从理论研究下手 。 为此 , 要求父亲收集并翻译当时颇具影响的世界四位建筑大师的理论与建筑实例 。 他们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 勒·柯布西耶 , 瓦尔特·格罗庇乌斯和密斯·温特罗 。
父亲得令后神采奕奕 , 像渴望驰骋的骏马奔向了天高地阔的草原 , 如涸辙之鲋返回了浪涛滚滚的江河 , 他的欢悦难以言喻 , 这是他的强项 。 这些大师的名字 , 在梁先生家的沙龙 , 在西单横二条的客厅 , 连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 。 虽不知甚解 , 却也闻知美国的赖特与法国的柯布西耶之间水火不容 。 梁先生对父亲说 , 他20世纪40年代去美国设计联合国大厦时 , 曾与赖特交谈 , 赖特见到梁先生大谈“凿户牖以为室 , 当其无 , 有室之用也” 。 并说你们中国数千年前的老子的一句话 , 就把建筑中最本质的矛盾讲清楚了 , 即空间是建筑中最主要的问题 。
赖特来自美国中部的大草原 , 祖先世世代代生于斯 , 长于斯 。 他崇尚土地原野、山川河流、森林和大自然 , 崇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 提倡“有机建筑” , 即今天我们说的绿色建筑 。 他所设计的“广亩城” , 实质是对城市的否定 。 用他自己的话说 , 是个没有城市的城市 。 认为大城市压根儿就该让其自行消亡 。 赖特受到美国和世界许多建筑师的追捧 , 成为国际建筑界耀眼的新星 。 我到美国时 , 堪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家的住宅据称是赖特建筑思想的产物 。 整栋建筑像只巨大的玻璃盒子 , 客厅里栽着茶花树和翠竹 , 潺潺流水从生满青苔的假山上流淌到山脚下的鱼池 , 又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小溪在竹丛边蜿蜒 。 仰靠在沙发上 , 透过玻璃棚顶看到白云在蓝天中悠闲徜徉 , 夜晚可以听到满天星斗的窃窃私语 。 卧室的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 , 如若不拉窗帘 , 完全感觉是睡在花丛里 , 窗外的绿树鲜花仿佛触手可及 。 在赖特的眼中 , 人们的住宅是大自然环境的延伸 , 住宅应保持人与自然的最亲密接触 , 与自然融为一体 。 这与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 , 当其无 , 有室之用也”一脉相承 。
我对建筑理论没有研究 , 更不敢以自己的无知而妄加评论 。 但我听到过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美国教授抱怨说 , 由于温室效应 , 夏天这玻璃盒子是个大烤箱 , 空调机要无休止地转动才能使人在里面安生 , 惊人的能源消费 , 让房主人无法心安理得 。 冬季也是同一道理 。 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 , 若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 , 这就让人心生疑窦了 。 但我不知这是否冤枉了赖特 , 这样的建筑是不是真是赖特的初衷?还是开发商对赖特的庸俗化理解?
勒·柯布西耶是著名的《雅典宪章》倡导人之一 , 也是法国现代派的建筑大师 。 他最早的建筑思想体现在马赛“太阳城”的设计中 。 1951年 , 他成为印度昌迪加尔市的总体规划师 。 1956年 , 他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南美高原上建设了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 , 被许多建筑师讥讽为“人性尺度失调和失控”的城市 , 一个完全不顾及国情和城市建设规律的城市 。 他在前苏联莫斯科设计的轻工业部大楼 , 被苏联人讥笑为“莫斯科的一个疮疤” 。 但在法国 , 他拥有众多的“粉丝” , 为了回敬各国建筑同行对法国建筑大师的不敬 , 法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不断地给他颁发各种奖章和荣誉证书 。 而勒·柯布西耶本人 , 却对他人的群起而攻之 , 尤其是对赖特挑衅性的出言不逊 , 表现出绅士的礼貌与静默 。
父亲说 , 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搞“四清”、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下 , 李正冠却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建筑界建筑理论的进展 , 渴望了解世界建筑流派的交锋 , 对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充满忧患意识 。 这既让父亲惊喜 , 也不免担忧;李正冠这样共产党干部中的异数 , 一定时时都如履薄冰 。 稍不留神 , 被匍匐在暗处的豺狗咬住 , 非死即伤 。 为此 , 一向不存防人之心的父亲也格外小心翼翼了 , 他守口如瓶 , 从不和他人谈李正冠要他翻译的文章内容 , 更不与任何人讨论建筑理论问题 。 父亲说:“我反正已经是死老虎 , 假如因为我的高谈阔论 , 给李正冠抹黑 , 罪莫大焉 。 这样一个干部 , 实属罕见 , 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大幸 。 ”
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马国馨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我们见到陈先生时那些急风暴雨的批判早已过去多年 。 ‘文革’时他五十岁 , 经过长期的锻炼和改造 , 也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 。 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谨慎小心 , 香烟抽得非常凶 , 帽子压得低低的 , 常穿的风衣还要把领子竖起来 , 紧紧裹在身上 , 一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样子 。 当然 , 我们对他也存着一些‘戒心’ 。 但在翻译组 , 却发挥他的语言优势做了大量的工作 。 ”(《建筑是不是描图机器》 , 陈占祥等著 , 陈衍庆、王瑞智编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戒心”两个轻轻带过的字 , 至今读来仍让人心中酸楚 。 可以想见父亲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之中工作 , 对一个“摘帽右派” , 周遭的人们仍时时存着“戒心”——无非是一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 。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 , 而是一个时代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 。 而在那样的环境中 , 李正冠给予父亲那样的信任和尊重 , 怎能不是重如泰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样做 , 但还是有这样做的人 。 这需要特殊的人格和禀赋 , 他要听从良知的呼唤 , 珍惜人性的光辉 , 摒弃私人的利害 , 才能穿越世俗的偏见和戒心 , 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 。
此后不久 , 李正冠匆匆找到父亲 , 非常简单地对他说:“设计院分到了几套房子 , 在建国门外的东光路 。 可能远了点 , 但我觉得你住得离设计院远一些更好 。 来得及就快搬吧 , 越快越好 , 夜长梦多 , 尽量别声张 。 这也许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了 。 ”
我们在“红八月”的革命风暴中 , 搬进了建国门外英国大使馆(当年叫英国代办处)旁边的一片新宿舍楼里 。 那是一片五层楼的宿舍区 , 除三间面积不算小的住房外 , 还有带煤气灶的厨房和一个可装淋浴的卫生间 。 阳台底下是“英国代办处”的院墙 , 站在我家阳台上 , 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 , 穿着泳衣泳裤 , 端着玻璃酒杯 , 在泳池边休憩聊天 。 虽然比不上西单横二条的房子 , 可比建筑设计院的宿舍大院好多了 。 更主要的是 , 在这片几十栋建筑的楼群里 , 住户来自各个不同单位 , 互不相熟 , 不再会有人踢开门就进去打家劫舍 。 44中的中学生能准确无误地瞄准我家 , 一定是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中有眼线 。 在红海洋遍地横流的“文化大革命”中 , 我们居然搬进了新居 , 就像世界被洪水吞没的那一刻 , 我们一家跳上了“诺亚方舟” 。 一向谨慎的李正冠 , 做如此决断 , 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 父亲说:“我此生此世即使不能还报他的情义 , 儿女们也要记住李正冠的名字 , 记住共产党里有这样一个人 。 ”写下这一切的时候 , 我想到了彭真 , 想到了彭真与梁思成的情义 。 人性应是党性的基石 , 身上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共产党员 , 首先是一个有骨有血、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 。 否则 , 一切都是扯淡 。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 , 李正冠刚刚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 , 就想把父亲调去北师大做英文教授 。 他自己领教了父亲的英文造诣 , 也希望更多的人受益 。 父亲婉言谢绝了李正冠的聘请 , 理由是他的宁波官话学生无法听懂 , 另外他不想离开自己的老本行 。 他希望有朝一日重操旧业 , 再展宏图 。
转载自公众号《老衲说说》
- 齐白石画山水:懂的人不多,骂的人却不少
- 一个人的长征:追寻孙子
- 晋朝电视剧为何只拍到司马炎登基统一三国,以后的事情为何不拍?
- 《圣斗士星矢》重病的伊利亚斯为什么还能对冥斗士产生重大威胁?
- 凿壁偷光的匡衡,后来怎样了?成了贪官为害一方
- 古代最有钱的县城大街,位于山西,现为世界遗产!
- 小脚的起源:为防疫古人如何解决大妈们串门、扎堆的问题
- 元宵节的由来与传说
- 自编教材评审的标准是什么
- 曹操有14个老婆,12个是抢来的寡妇,一代枭雄为何爱抢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