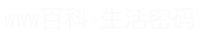亚非会议后北京酒会准备得过于简单 总理做自我批评
在中华民族最需要周总理的时刻 , “四人帮”的魔爪夺去了他的生命 , 而周恩来同志并没有离开我们 。 犹如日月千秋 , 松柏长青 , 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
1949年8月 , 古老的北京城沉浸在新生的欢乐之中 。 这年我22岁 , 随同刘少奇同志和他带领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一起从沈阳来京 。 作为一个青年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夕进了首都 , 又在丰台火车站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 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首长前来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少奇同志和同车进京的200多名苏联高级顾问 。 他不象我们曾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 络腮长须、飞行员的装束 , 而是一身米黄色的中山服 , 神采奕奕 , 英俊非凡 。
人接到了 , 车队已准备进城 , 本以为周恩来同志也就要回去了 。 我想错了 , 他没有即刻离去 。 他在师哲同志的陪同下 , 顺着月台漫步走向我们乘坐的车厢 。 这节车厢里有十几位苏联妇女 , 他们是当年中长铁路沈阳分局苏联职工的家属 , 自愿参加专列餐车的服务 , 照料首次来华的苏联朋友 , 由分局长杜拉索夫带队一起来京 。
“快看!周恩来向我们走过来了 。 ”不知是谁这么轻声一说 , 车上的人都坐不住了 , 个个争着下车 , 前去握手问候 。 周恩来同志看到我和杜拉索夫站在一起 , 过来同我们握手 , 并问我:“你这个小鬼是搞什么工作的?”不知当时是由于高兴 , 还是紧张 , 我傻呼呼地只顾整理衣扣 , 忘了及时回答 。 师哲同志从旁插话:“我们在沈阳开干部会欢迎专家的时候 , 这个小伙子参加了几次翻译 。 ”总理一听 , 微笑着说:“噢 , 那好啊 , 现在很需要有一批年轻的同志来搞俄文翻译 。 ”
一
1949年 ,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之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东方大地上诞生 。 新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任务 。 在这个庞大而又极为复杂的领域里 , 充满了大量的新课题 。 历史本身决定了我们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 , 只能首先学习苏联 , 借鉴他们的经验 。 这年夏天 , 刘少奇同志访苏回国时带来的那批苏联高级顾问 , 大多数都是在苏联各部门、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经验丰富的专家 。 首席顾问科瓦廖夫(我们称作总顾问)曾是苏联交通部部长 , 卫国战争时期是一位将官军衔的运输指挥员 。
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苏联专家来华支援我国的建设事业 , 给予了高度重视 。
1949年 , 十月革命节前夕 , 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到铁狮子胡同专家寓所出席了专家们的庆祝集会 。 毛主席讲了话 , 欢迎专家 , 祝他们工作得好 , 生活得好 。 我党中央政治局许多位领导人亲临寓所参加集会 , 全体苏联专家深受鼓舞 。
有关苏联专家的全部工作 , 始终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 。
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 , 但自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进京之日起 , 他仍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 亲自关心苏联专家们的工作和生活 。 他讲:“苏联专家千里迢迢来中国帮助建设 , 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 做好我们自身的各项工作 , 发挥他们的作用 。 ”
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住的宽街铁狮子胡同寓所 , 是一座十分雅静的传统式大庭院 。 1949年10月间 , 周恩来到这里看望专家们 。 他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很需要专家的帮助 , 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 不过 , 他们刚来不久 , 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 。 我们可以请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给他们介绍情况 。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部署 , 陈云同志在这里主持了两次重要的会见 。 当年中财委和文教委系统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 , 同苏方组长以上的专家骨干会见 , 建立了各自对口的工作联系 。 彭真同志在政法口主持了同样的会见 。 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吕正操等领导同志有时到这里与科瓦廖夫谈话 , 交换意见 。
为了加强对专家工作的日常领导 , 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指定由伍修权、杨放之两位领导同志牵头组成专家工作小组 , 以便及时了解情况 , 调查研究 , 监督检查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 。
从1953年起 ,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 , 逐步建立健全了专家工作的组织机构 。 在国务院内设立了专家工作办公室 。 1954年与原有机构合并 , 成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外国专家工作局 。 为了总结和交流专家工作经验 , 在内部发行《专家工作通讯》 , 刊名就是周总理题写的 。 此外 , 定期用俄文发行《内部参考资料》 , 以便苏联专家更及时地了解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 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外专局局长杨放之同志定期地向经济和文教两方面的总顾问介绍我们的情况 。 这些做法和措施对加强中苏双方同志们的了解 , 加强合作都是有力的推动 。
科瓦廖夫平时在寓所召开会议 , 听取汇报较多 。 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 , 1950年奉调回国 。 此后 , 来华接替他工作的 , 在经济专家方面 , 先后有阿尔希波夫和毕考尔金 。 这两位总顾问同我国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一直很好 。 1952年周总理出访苏联的时候 , 毕考尔金和当年中财委计划局的几位专家奉召到莫斯科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 。 他们对于苏援项目问题 , 特别是在聘请专家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 协助陈云、富春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 周总理表扬了他 , 说他在聘请专家问题上帮助我们做了很好的努力 , “人数削减了 , 而专业更加对口了 。 ”
我国各有关部门(包括基层)也经常请苏联专家做报告 , 做讲演 , 或举行学习班 , 介绍苏联的经验 。 许多专家的报告、演讲材料或建议方案都是很有价值的 , 很受中国同志们的欢迎 。 可是 , 也有些专家的报告内容谈原则多 , 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不太适用 , 甚至有人做报告引语连篇 , “洋八股”很浓 。 这些报告或讲演是不大受欢迎的 , 因为这样的内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 而且方法本身也是不成功的 。
为此 ,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的情况 , 委托外专局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领导同志向全体专家做报告 , 他本人首先带头这样做 。 他除了亲自到国际饭店礼堂向全体在京苏联专家做政策报告之外 , 有时在国内给有关部门做报告的时候 , 也通过外专局组织苏联专家参加 。 有一次 , 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工交口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做报告 , 阿尔希波夫等近百名苏联专家都听了 。 在这次报告中 , 周恩来同志阐明了当年我们关于“一长制”的看法 , 强调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既借鉴苏联的经验 , 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厂矿管理体制 。 周恩来同志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即将期满回国的文教专家 , 在讲话中 , 又一次谈到:“学习苏联经验不能有教条主义 , 照搬过来的东西是不适用的 。 ”
总理的这些讲话深受苏联专家们的重视 。 应该说 , 长期以来苏联专家在中国与各部门的同事一道合作 , 朝夕相处 , 关系是很好的 。 在这方面 , 我国的冶金部、煤炭部、铁道部等部门都取得过好的经验 。 在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总理的表扬 。
随着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 苏联专家的人数日益增加 , 所涉及的方面也更加广泛 。 在我国各部门的实际工作过程中 , 如何对待援华的苏联专家问题 , 逐渐反映出两种比较明显的思想倾向:一种是过分依赖专家 , 对苏联的经验机械地照搬 。 这是主要的倾向 。 另一种是某些部门或单位把专家请来了 , 但没有很好地使用 , 有的专家来华后一时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 两种倾向实质上反映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 即在中苏关系最盛期 , 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 。
周恩来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 , 针对具体实践中出现的倾向 , 就有关苏联专家工作问题 , 先后有过多次重要的指示 。 追忆他所阐述过的指导思想 , 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
(一)学习苏联经验不可机械照搬 , 要结合我国实际消化运用;原则方针问题 , 必须自行决策 , 不能依赖苏联专家 。 (二)对全体专家要热情相待 , 主动介绍情况 , 认真研究分析专家们的建议 , 不能给坐“冷板凳” 。 (三)顾问要减少 , 根据急需聘请专业对口的技术专家 。
总理的这些指示从原则的高度明确了我国对外国专家的基本政策 , 并成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这些指示精神曾分别体现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外国专家工作的规定之中 。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了 , 不论双方有多少意见分歧 , 不论事物有多大的曲折 , 赫鲁晓夫一道命令把全体苏联专家统统撤走 , 这实在是太不识事务 , 是倒行逆施 , 损伤了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 。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全体苏联专家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 , 他代表中国人民表达了惜别的心情 , 表示苏联专家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 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 在西花厅接见阿尔希波夫的时候 , 周总理亲手给他授予了友谊纪念章 。
二
凡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有感受:他作为领导者在工作中对每位工作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 , 而作为同志对每位工作人员则是十分体贴和爱护 。 尤为珍贵的是 , 他严于律己 , 遇事当众做自我批评 。
1952年在莫斯科 , 周总理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 , 他把马列同志和我找了去 , 问道:“你们说说 , 49加3等于多少?”一下把我们问愣了 , 细细一算才明白 , 经我们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 。 总共应该是52 , 而不是53 。 他批评得好:“不能马虎 , 文件一旦送出 , 连算数都有误 , 人家岂不笑话 , ……”我们脸上火辣辣的 , 而心里感到温暖 。 他如此细致 , 我们很受触动 。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 , 周恩来同志对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亲自过问 , 抓得很紧 。 他委托章汉夫和炳公(王炳南)逐项检查落实 。 组织模拟演习采访人员招待会 , 发言人黄华与“外国采访人员”逼真地对话 , 段连城、李肇基等优秀的译员也都反复操练 。 代表团的英、法、俄语译员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 , 照样一个一个地进行专项考核 , 直至每人的总平均分数合格 。 副外长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太好 , 而当年的专机又小 , 在蒙古上空颠簸比较厉害 。 恩来同志安排他先乘火车经满洲里到伊尔库茨克再接续航程 。 他把我找去 , 一再叮嘱 , 要我配合黄树则同志一路精心照料 , 特别是进入苏联境内 , 更要与苏方保持联系 。 直到在伊尔库茨克见了面 , 克农同志的健康一切正常 , 总理才放心了 。 到了日内瓦总理下榻在万花岭别墅 , 他把随同工作人员(包括司机、打字员、洗衣工人)的食宿安排都看了一遍 , 自己方去休息 。 并向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其他主管领导交代:“大家都是第一次来 , 工作又很辛苦 , 食宿条件要搞好 , 不要只顾我……” 。 会议进行期间 , 总理要我们整理一份某些代表团对协议草案的意见 。 陈家康、马列和我承担这件事 。 我们搞好一份打字稿送给了他 。 恩来同志一看 , 把马列和我找了去 , 说:“看得出你们是花了些功夫 , 整理得很干净 。 可这怎么行呢?我不是要材料好看 , 而是要知道原文是什么样 , 现在是怎么改的 , 要能比较 , 这样才便于分析研究其中的变化……”我们把这份不合格的卷子拿了回来 , 重新进行了整理 。 这次合格了 , 可他却说:“让你们重来了一遍 , 这怪我事先没有交代清楚……” 。
亚非会议之后 , 总理在北京举行酒会 , 招待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 。 酒会准备得过于简单 , 几碟糖果、炸土豆片和花生米 。 总理不甚满意 。 散会后 , 他没有责备工作人员 , 而是说:“这事怨我布置得不细 , 首先由我负责 。 ”贺老总在一旁着急了 , 插话说:“这怎么能怪总理呢!外交部节约应该 , 可也不能到这种地步 。 ”事也巧 , 就在这个时候 , 缅甸使馆的一位参赞匆匆忙忙跑上楼来 , 说他夫人走丢了 , 上楼来找 。 他一看周恩来同志正在大厅讲话 , 赶忙鞠躬道歉 , 忙着退出去 。 总理对他说:“没有关系 , 我们是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 如果你愿意 , 可以听……”
1965年春天 , 五一节刚过 , 西花厅的几位同志陪着总理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来 , 在前庭过道上我与他迎面相遇 。 他问我:“你都在忙些什么?怎么不常见你?”我回答说已经调动了工作 。 他又问:“调哪儿去了 , 搞什么?”我说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教务行政工作 。 “嗅!那俄文可不要丢了 , 很有用啊!”说完还叮嘱我要把新任的工作搞好 。 想不到 , 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同周恩来同志的几句对话 。
“文化大革命”初期 , 总理先后三次到二外视察 。 这时候我已经“靠边”了 , 只见他在礼堂里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 , 还见到他在职工食堂吃午饭 。 自己出粮票 , 自己付钱 。 更想不到 , 这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
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 。 当年 , 我被剥夺了向他老人家遗体告别的权利 , 更没有可能去护送灵枢 。 我站在复兴门马路的台阶上 , 望着灵车徐徐西行 , 我的心与千百万群众泪水浸透的心汇合在一起 , 共声呼唤 ,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 您不能离开我们 , 您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的周总理》
- 晋朝电视剧为何只拍到司马炎登基统一三国,以后的事情为何不拍?
- 凿壁偷光的匡衡,后来怎样了?成了贪官为害一方
- 评职称课题最后一名有用吗
- 徐向前,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 他是四野三纵的政委,曾因升迁速度太快不得不请示,后授衔中将
- 浅谈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权:挣扎还是静待结局?
- 一支五万大军突然消失,2500多年后,在一处洞穴被发现
- 秦朝那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鼠年说鼠(8)
- 雍正死后竟与年世兰合葬在一起,雍正的陵墓为何从未被盗?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