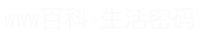重读“钓鱼城”——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重读“钓鱼城”——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重读“钓鱼城”——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
▲钓鱼城南水军码头航拍 。 袁东山供图

重读“钓鱼城”——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
▲钓鱼城发掘出的铁火雷 。 本报采访人员刘恩黎摄

重读“钓鱼城”——一座小山城何以改写亚欧大历史// //
▲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 。 袁东山供图
新华社北京5月17电(采访人员李勇、张桂林、刘恩黎)5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的报道 。
公元1260年,席卷西亚,先后攻灭阿拔斯王朝、占据叙利亚,兵锋直指埃及的蒙古大军,突然勒马不前,主力军团挥戈东返 。
前一年,在相隔万里的东亚大陆,南渡长江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昌)、震动江南的忽必烈大军,于破城在即时,遽然退兵北还 。
气势如虹、横扫亚洲的蒙古铁骑,几乎在同一时期如潮水般退却 。
而这一切都因为自中国西南嘉陵江畔传出的消息:率军进攻四川,意图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城遭到顽强抵抗,于1259年农历七月身亡 。
蒙哥死后,汗位空虚,蒙古诸王纷争遂起,各军团匆忙从亚、欧战场回撤 。 命悬一线的南宋王朝,暂时得免灭国之祸,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因此改变 。
700多年后,在重庆合川嘉陵江畔的钓鱼山上,一条攻城地道、几段御敌城墙、数十枚铁火雷残片,尤其是一座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的发现,使这里跻身“201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下,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座曾改写亚欧历史的传奇城堡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
西南一柱:防御体系关键支撑
自长江、嘉陵江交汇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西折、北进,溯嘉陵江上行90余公里,就来到了古称合州的滨江之城重庆合川 。 在合川城东部,一座最高海拔近400米的钓鱼山,伫立在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的半岛之上 。
依山就势的钓鱼城巍然屹立于山巅,北、西、南三面峭壁悬崖据江而立,险绝异常 。 这里曾见证波及亚欧大陆的金戈铁马、滚滚烽烟 。
1235年,蒙古大军在西征东欧、东征高丽的同时,大举出兵南下攻宋 。 自此,双方在西起川陕、中抵荆襄、东至江淮的三大战场,展开数十年攻防 。 因地处长江上游,东扼夔门天险,顺江可趋吴楚,巴蜀地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蒙古攻宋的首要目标 。
为稳固“西门”“后户”,1242年,南宋朝廷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 。 鉴于成都已失陷,川中残破,余玠兼知重庆府 。 重庆由此成为全川抗蒙的军政大本营 。
遏阻蒙古军继续南下据长江破夔门,成为余玠到任后的头等大事 。 他“集众思,广忠益”,充分运用巴蜀山险对抗蒙古的骑兵优势 。 1243年,命人筑城于嘉陵江下游三江交汇、重庆正北的合州钓鱼山上,并迁合州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戎司于此,驻以重兵 。
同时,相继在川东各山隘建山城数十座,最终形成以嘉陵江、长江为依托,以重庆为核心,以点控面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 。 地处“蜀口形胜之地”、屏障夔渝的钓鱼城,则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支撑 。 余玠帅蜀期间,多次以钓鱼城为前线指挥中心,联动各山城,率领宋军与蒙古军在四川开展攻防,“多有劳效” 。
此后数十年间,来自秦、陇、蜀地的数万南宋军民据险坚守钓鱼城,“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使这里成为拱卫南宋“西门”的坚强堡垒,并在蒙古第二次大规模进兵灭宋的紧要关头,奋起抗击,扭转乾坤 。
700多年后,当人们走近钓鱼城时,眼目所及,山险依旧,但城下缠绵环抱、波澜不惊的江水,城里茂林修竹、清幽宜人的山色,让人很难将这里与蒙宋古战场相连 。 几经复建的城门、城墙、马道、校场,也难辨年代和真伪 。
历史的烽烟,似乎已不可触摸 。 人们难以想象,眼前这个弹丸之地,在13世纪,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36年,及至南宋灭亡,仍然屹立不倒?
即便在专家学者看来,钓鱼城战役和山城防御体系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但多囿于史料,缺乏考古实证支持,还有诸多困惑与疑团待解 。
“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却活在许多无从考证的典故和传说中,真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 ”痴迷于蒙宋之战的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暗下决心:不能让人们之于钓鱼城的疑惑继续无解 。
2004年,钓鱼城考古发掘全面启动 。 此后15年里,袁东山和同事们踏遍钓鱼山方圆20余平方公里,试图找出掩盖在历史迷雾里的“英雄钓鱼城” 。
史料显示,元军最终占领钓鱼城后,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拆毁 。 清代,当地为抗击白莲教,局部利用蒙宋战争期间的钓鱼城址进行了复建 。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专家结合文献研究复原了钓鱼城,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区分钓鱼城的宋代城垣和清代城垣 。 上世纪80年代,当地为发展旅游又新建了部分城墙和设施 。 这些都给前期考古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
“我们首先就要辨识宋代石料开采加工、城墙砌筑方式等留下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探寻蒙宋时期的钓鱼城 。 ”袁东山说,加上钓鱼山范围很广、险峻崎岖、植被茂密,踏勘和测绘难度很大,“大概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钓鱼城城墙的平面分布图 。 ”
通过时代甄别和空间重构,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南宋钓鱼城比保留至今的清代城体系宏大很多 。
“不仅守山而且控江 。 ”袁东山说,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误解——认为古钓鱼城就是现在看到的钓鱼山顶2.5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 。 “事实上,蒙宋战争时期的钓鱼城,是一个‘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 。 ”
“钓鱼城之妙首先体现在‘地利’上 。 ”袁东山说,它既利用了山江之险,又有沟通之便 。 城池选址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处,南、北、西三面环水,是控扼长江上游的咽喉要道;其山峰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200余米,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面则有堑沟阻隔 。 钓鱼城四周山麓田地广阔,还有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使之具备了蓄积人力物力、长期坚守的基础 。
最为关键的是将人力与天险融合,防御体系精心巧妙 。 考古队发现,南宋筑城者们沿钓鱼山南北山麓,修筑了两道奇特的“一字城墙”,分别延伸至山脚江边的水军码头,如同从山顶伸出的两只手臂,拽住长达20公里的嘉陵江,形成了“控山锁江”的坚实屏障 。
“一字城墙完全隔断了钓鱼山东西交通,有效阻碍了城外敌军运动;通过拱卫水军码头,又将宋军的水军优势最大化,压制擅长陆路作战的蒙古骑兵,同时也保障了钓鱼城的水上后勤补给线 。 ”袁东山表示 。
在考古人员一锹一铲发掘下,南宋钓鱼城防御体系的“拼图”逐渐清晰:以钓鱼城山顶环城和南北一字城为核心,利用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势控扼三江,北西南三面环绕的江水形成天然护城河,东面则利用山冈、堑沟、城墙阻隔 。 南北水军码头筑起水上防线和补给线 。
于是,钓鱼城延伸成为10余平方公里的半岛防御整体,从而有效担负起屏障重庆、控御东川作用 。 恰如南宋蜀人阳枋赋诗所言:“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 。 自昔无城当蜀屏,从今有柱壮坤舆 。 ”
大汗殒命:铁火雷所伤致死?
1251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继承汗位 。 雄心勃勃的蒙哥大汗,决心建树功业 。 在相继派出诸王西征西亚、东征高丽、远征大理国后,又谋划以左、右两路大军,会同已占据云南的军队,大举攻宋 。
蒙哥决定亲率右路军经关中进攻四川,企图攻取重庆,东下夔门,与左路军和南翼军会师于鄂州,再顺流东下,直捣临安,灭亡南宋 。
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统精兵四万、号称十万大军,自六盘山挥师南下 。 此时主持四川防务的一代名将余玠,因受疑于南宋朝廷已自杀身亡多年 。 由于宋廷政治腐败,继任帅蜀者,皆无大的作为,四川山城防御力量大为削弱 。
蒙哥一路过汉中、入利州,取苦竹隘、拔长宁山城,降大获、青居、大良诸城 。 1258年底,沿途汇集而至的约7万蒙古军,沿嘉陵江南下进抵合州,兵锋直指重庆 。
在攻破合州旧城,切断钓鱼城与周边山城联系后,1259年农历二月,蒙哥以“困守环攻”战术,督率水、陆诸军持续围攻钓鱼城 。 但在南宋守将王坚的带领下,钓鱼城守军据险抗击 。 蒙古军围城数月仍不能克 。
据《元史》记载,农历二月三日,蒙哥督诸军战钓鱼城下 。 七日,蒙古军从东面猛攻一字城 。 九日,猛攻镇西门,均不克 。 农历三月,从东、北、西三面对东新门、奇胜门和镇西门外的“小堡”发起强攻,再次失败 。 农历四月,接连20天大雨,暂停攻城 。 二十二日,强攻护国门,败归 。 二十四日夜,绕道西北进攻外城,一度登上城头,但最终被打退 。 入夏后,暑热至,蒙古军“军中大疫”“士马不耐其水土” 。 农历六月,征蜀前锋将汪德臣在战斗中受伤身死,蒙古军锐气大挫 。 农历七月,转战东西、纵横南北的一代骄子蒙哥大汗,也“崩于钓鱼山” 。
丧失主帅的蒙古军迅速北撤 。 同年农历九月,南宋朝廷宣布“合州解围”,钓鱼城战役结束 。
蒙哥大汗的死讯辗转传往长江中游及西亚后,蒙古军的征伐顿时失去了势头 。 征西亚的旭烈兀、攻鄂州的忽必烈等部军队,陆续回撤 。
但钓鱼城之战中,蒙哥大汗到底因何而死?史料记载莫衷一是 。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自农历六月起即“不豫”,至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 。 拉施都丁《史集》记述,蒙哥因水土不服而得了赤痢,为对付病症,他坚持饮酒,使“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终于死于“那座不祥的城堡下” 。
病死说之外,也有受伤致死的说法 。 明万历《合州志》所引无名氏《钓鱼城记》称,蒙古军在“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 。 城内宋军“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桅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 。 亲临现场督战的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 。 在去重庆缙云山寺途中,“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 。
蒙哥之死,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 。
十多年来,袁东山和队员们在钓鱼城古战场上,也为解开这个历史谜团,寻找着蛛丝马迹 。
2005年,在钓鱼城西北的古地道中,考古队员发掘出80余片弧形铁器残片,经确定是铁火雷爆炸后的碎片;2013年,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出土一枚铁火雷爆炸后的弹片,2017年又在该遗址出土铁火雷残体一枚 。
结合技术测定和史料分析,考古人员认为,钓鱼城战役中,蒙古军开凿地道想以“地突”战术攻城,而宋军则以铁火雷御敌 。 由发现小弹片的数量推测,当时投入战斗的铁火雷,可能数以百计 。
采访人员日前在考古现场看到,2017年出土的这枚铁火雷残体呈圆球形,直径11厘米、壁厚约1厘米,差不多有一个脐橙那么大,采用硬度非常高的白口铸铁作外壳,内腔用于填充火药 。 “这些铁雷外观设计精巧,内置药线引爆,有着相当威力,在当时的战场上可谓是安全、精准、高效的先进武器 。 ”袁东山说 。
袁东山介绍,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到宋代已演进为初级火器 。 北宋出现火药箭和火球,南宋创制出铁壳火球——铁火炮和各种火枪 。 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战场上,开始弥漫炮火与硝烟 。
据文献记载,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曾伯提及,荆州每月生产“铁火砲”在1000-2000件,库存多达十几万件;开庆元年至景定二年,建康府知府马光祖提到,建康府在两年时间内,生产火攻器具6万余件,其中各种规格铁砲壳3.5万余件,平均每月也有1000多件,“由此推断,宋蒙战争期间的山城,铁火雷产量也应是非常大的 。 ”
“此前发现的宋代火器实物少之又少,钓鱼城的这些发现,为宋代火器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 。 ”袁东山说,更重要的是,铁火雷的发现,也为蒙哥死因的学界争议,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
据明万历《合州志》记载,“宪宗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 。 ”既往认为,“炮风”为发射的礌石所致 。 元代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1280年扬州炮库爆炸事件时,也提到“炮风”“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袁东山认为,从文中推断,“炮风”应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结合钓鱼城发现的球形铁火雷,蒙哥大汗有可能是被铁火雷类火器炸伤后死亡 。 ”
“护国城头飞炮烈,温泉寺内大王横……”火器在钓鱼城之战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袁东山看来并非偶然 。 他表示,通过多年考古发掘,重庆地区的南宋球形铁火雷遗存不断被发现,说明这种火器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着成熟的制造技术,且在战争中得到普遍应用 。 这种先进的武器对当时局部战役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
百战弥坚:长达36年坚守的秘密
巍巍钓鱼山,碧血映烟云 。 当年那场使蒙古大汗殒命,牵动亚、欧格局的战役中,乃至在长达36年的坚守中,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枢纽和指挥中心在哪里?他们又是如何指挥若定,以弱胜强,创造奇迹的呢?
史载,蒙哥大汗攻蜀时,合川钓鱼城守将为南宋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王坚 。 王坚自1254年莅任后,对钓鱼城进一步加固,筑南北一字城,兴修水师码头,在城内建池凿井,同时利用钓鱼山良田千亩“保民练武”、且耕且战,聚集秦、陇、蜀地退守而来的军民十数万人,“人物愈繁、兵精粮足” 。
“钓鱼城之战堪称世界战争史上要塞防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 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找到作为防御指挥中心的州治、戎司衙署 。 ”袁东山说 。
2012年,考古人员在对钓鱼城南一字发掘中,发现城墙随山势升高到半山后,变成垂直高起二三十米的断崖,而断崖之上又发现东西两道城墙,与断崖面一起,形成南一字城的内城 。
按照常规,内城东边的城墙迎敌面朝东,西边的城墙迎敌面朝西,但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西边城墙迎敌面仍然朝东 。 这似乎在提醒,南一字城内城以西的区域,才是防守的重心所在 。
结合此前在钓鱼城西北发现的蒙古军为突袭攻城挖掘的地道,袁东山意识到,钓鱼城西部山腰处的范家堰,可能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区域” 。
2012年8月,袁东山顺着尚未发掘完毕的一字城城墙朝西走,在人迹罕至的范家堰,他举目四望,这里位于钓鱼山二级台地上,背倚山顶,面朝嘉陵江,整体隐藏在主峰之下的山坳中,台地之外即是落差近30米的陡峭悬崖 。 可以想见,当时蒙古军队从山下仰视很难发现这一区域,这里也处在炮火、弓箭的射击死角,易守难攻,正是指挥中枢的理想之地 。
“那天是19号,经过探勘和试发掘,建筑残垣逐渐露出,我兴奋得中午饭都没吃下 。 ”袁东山说 。
随着范家堰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 。
采访人员在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看到,这一遗址主要由东部的前、中、后三进院落,及西部水池亭榭等两部分景观建筑构成 。 院落依山呈阶梯式构筑,整体高差达16米,设计巧妙 。 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随处可见 。
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介绍,已经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厢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144处,出土宋代瓷器、铁器、炮弹残片等标本1100余件 。 园林景观部分还发现了水池、石灯,艺术价值相当高,其中一座在当时只能建于皇宫和孔庙中的乌头门遗址,更凸显出范家堰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
“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建筑遗迹信息,可以认定,范家堰遗址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南宋合州衙署、兴元戎司所在地,也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 。 ”袁东山说,范家堰衙署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宋衙署遗址,价值重大 。
“大军压境之际,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不仅体现了宋代能工巧匠们的建筑造诣,也彰显出当时人们沉着应战强敌的自信和决心 。 ”袁东山感叹道 。
据史料记载,钓鱼城之役,在长达5个月的攻城战中,蒙古军虽然“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却“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只能派出小股人马履崎岖以登,冒险强攻,结果不是因为士卒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由于后军不继而败退 。 据《元史》记载,尽管蒙古军有几次攻破外城,甚至一度登上城头,“伤宋兵甚重”,但始终无法突入钓鱼城核心区域 。
反观钓鱼城守军,则是士气高涨、斗志正旺 。 万历《合州志》引《钓鱼城记》记载,宋军一度发炮,向城外抛掷各重30斤的鲜鱼二尾、蒸面饼数百,并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 ”守将王坚更是白天率军抵抗,夜晚不时派兵袭扰敌营,使得蒙古军夜不安枕 。
“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那么范家堰衙署遗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 。 ”袁东山说,正是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精良的防御布局,钓鱼城守军才能在对抗蒙古大军的战斗中创造出奇迹 。
落幕与回响:探寻仍然没有止步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改变先取巴蜀的灭宋战略,逐渐把进攻重点转移到长江中游的荆襄战区 。 蒙宋双方在四川战场进入相峙状态 。
作为重庆前哨的钓鱼城,与嘉陵江、长江沿岸诸多山城相互支持、依存,足以控扼东川,因而仍是蒙宋争夺的焦点 。
1268年起,忽必烈先后调集近十万大军围襄阳,开始了长达5年的襄樊之役,也揭开了蒙古第三次征宋的序幕 。
为牵制南宋从巴蜀调兵援助襄阳,蒙古军在四川开展大规模袭扰,尤其加强对钓鱼城的包围,并在钓鱼城与其他山城之间“筑城进窥” 。 但钓鱼城守将张珏战守有力,“往往出奇制胜,斩获累捷 。 ”直至襄樊战役结束前,蒙古军在钓鱼城只能“春去秋来,出没无常” 。
奈何历史的车轮终归无法阻挡 。 1273年,元军进占襄阳后,忽必烈下诏水路并进,大举灭宋 。 四川诸多城镇也相继被元军取得 。 1276初,南宋朝廷在临安降元 。 元军也加快了平定四川的步伐,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陷泸州、平东川 。 1278年农历二月攻破重庆城,绍庆、南平、夔、施、思、播等州皆下 。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 1279年正月,钓鱼城守将、合州安抚使王立,以不可屠城为条件终止抵抗,开城降元 。 为南宋坚守了36年的钓鱼城,至此最后陷落了 。 同年,逃至崖山的幼帝赵昺,蹈海而死,南宋灭亡 。
渝水悠悠,孤城无言 。 烽烟散尽的钓鱼城,如今像一位英雄迟暮的巨人,静卧在波澜不惊的嘉陵江畔,任那惊天动地的热血与炮火,掩埋于厚厚的尘土和时间的长河 。
范家堰遗址的发现,无异于一次穿越时空的唤醒 。 让这座创造历史的英雄城再次鲜活起来 。 随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钓鱼城的军事、文化、历史乃至世界性价值和意义,逐渐开始显现 。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让这座宋蒙(元)时期的英雄城,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 ”袁东山认为,作为蒙宋战争的重要节点,钓鱼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功遏制住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进攻,彰显出南宋军民坚忍顽强、忠贞不渝的精神气节 。 钓鱼城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也是一座精神宝库 。
这座城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延长宋祚20余年 。 正如明代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 。 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
而且,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内乱,直接导致了元朝的建立,蒙古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也基本结束,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 。
钓鱼城的军事价值也不言而喻 。 “钓鱼城防御体系是中国积极防御思想的集大成者 。 ”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奚江琳认为,作为世界重要的军事遗产,钓鱼城集中体现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展现了东方战争智慧和积极防御的战斗精神 。
钓鱼城还让人们见到了我国“火器鼻祖”的真实面貌 。 “中国最早期的铁壳爆炸弹‘铁火雷’,是古代中国在火药火器领域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表示,钓鱼城出土的南宋铁火雷残片,不仅为火药火器发明史研究提供了长期缺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而且为深入探讨13世纪的战争史、军事史提供了新的物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如今,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钓鱼城古战场,正在经历“重生” 。 作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钓鱼城已经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 。 2019年3月,重庆市向国家文物局提出钓鱼城遗址申遗正式申请 。 今年下半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将启动建设 。
但关于钓鱼城的进一步探寻仍然没有止步 。 “考古揭露硬遗址,解读软文化 。 ”袁东山告诉采访人员,在继续做好范家堰遗址研究的同时,还考虑对一些文献记载不多的关键点位、矛盾点位进行勘探发掘 。
对钓鱼城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展示和传承,也越来越让袁东山“操心”,“让大众可以轻松读懂钓鱼城遗址的空间特征,理解蒙宋战争的历史现象,感悟宋人的精致生活,传承钓鱼城守将的忠勇精神,是下一步想着力做的 。 ”
“钓鱼城发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和间接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 关于钓鱼城价值的研究,还应该深入和强化 。 ”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的发言,引起广泛共鸣,“应站在更高层次、从全世界层面来审视这场战争和这座山城 。 ”(完)
- 别不信,最早把牡丹叫“国花”竟然是她!
- 本命年不顺利,要挂红“辟邪”,为何人们这么认为?
- 历史上诸葛亮究竟是否有过“七擒七纵孟获”?
- 秦朝那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鼠年说鼠(8)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
- 返京者深夜有家难回:“硬核防疫,以人为本”,为何这并不矛盾?
- 古代名画里的“女主角”,每个都是一段历史
- 河北的省级博物馆为何叫“河北博物院”,而不是“河北省博物馆”
- 历代皇帝为何自称“朕”?恍然大悟!
- 《出师表》成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上推崇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