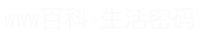罗新:北魏“西郊祭天”是什么样的?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罗新:北魏“西郊祭天”是什么样的?
公元494年 , 北魏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 , 这标志着他领导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改革 , 达到了一个顶峰 。 然而在迁都之前 , 孝文帝就已经废除了一些原有鲜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 其中就包括“西郊祭天”仪式 。 自此之后 , 这种传统拓跋鲜卑特色的祭天仪式 , 就消失在历史之中了 。 过去历史学界对于北魏的祭天仪式往往一笔带过 , 认为只是普通的祭天仪式 。 然而 , 搞清楚北魏“西郊祭天”到底是什么样子 , 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内亚人群的政治、文化构造 。
近日 ,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以《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为题 , 讨论了北魏西郊祭天仪式中特别“小”的一个物件——祭天方坛上插着的木杆 。 罗新把这些木杆回归到内亚传统的历史源流 , 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于中国历史中内亚传统的认识 。 (内亚包括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地区 , 罗新研究的内亚人群通常指使用阿尔泰语系的人群 , 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都属于内亚人群 。 )

罗新:北魏“西郊祭天”是什么样的?// //
罗新
《魏书·礼志》的记载 , 北魏皇帝会在每年四月初四祭天 , 而且在祭天的方坛之上 , 会立一些名为“天神主”的木杆 。
“女巫执鼓 , 立于陛之东 , 西面 。 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 , 在巫南 , 西面北上 。 女巫升坛 , 摇鼓 。 帝拜 , 后肃拜 , 百官内外尽拜 。 祀讫 , 复拜 。 拜讫 , 乃杀牲 。 执酒七人西向 , 以酒洒天神主 , 复拜 , 如此者七 。 礼毕而返 。 自是之后 , 岁一祭 。 ”
“天神主”在《魏书·礼志》中又被称作“木主”:“天赐二年夏四月 , 复祀天于西郊 , 为方坛一 , 置木主七于上 。 ”
“木主”、“天神主”这些名词指向的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周礼·春官·司巫》注 , “主 , 谓木主也……神所馆止也 。 ”北魏人所立的“木主” , 应当就是用于祭祀的木杆 。
这些木杆的在北魏祭祀中 ,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魏书·礼志》记载过另一件事 , 北魏曾意外发现其先祖生活祭祀过的山洞(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 , 于是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 “敞等既祭 , 斩桦木立之 , 以置牲体而还 。 ”在这场祭祀中 , 北魏官员们砍伐了一些桦木插在地上 , 用于放置祭祀用的牲肉 , 所以祭天的“木主”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作用 。
祭祀时把肉挂在木杆上 , 这在世界上不同时代很多文化中都出现过 。 罗新认为不需要寻找很遥远的例子 , 他尝试着在北魏所处的内亚的传统中 , 寻求这种现象的解释 。 研究中国历史时 , 多增加一种内亚的视角 , 不能确保是对的 , 但可以多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 。
罗新首先介绍了蒙古人的祭祀 。 《蒙古秘史·卷一》记载一种名为“主格黎”(?ügeli)的仪式 , 明朝人的旁译就是“以竿悬肉祭天” 。 此外还有“主格黎迭扯” , 意为“以竿悬肉祭天处” 。
但是 , 匈牙利东方学家李盖提认为 , “主格黎”这种仪式是祭祀祖先 , 而非祭天 。 他的理由是 , 《蒙古秘史·卷一》记载 , 父亲死后 , 沼兀列歹被认为不是孛端察儿的亲生儿子 , 就被剥夺了参加“主格黎”仪式的资格 。 因此 , 很显然“主格黎”是只有家族成员才能参与的祭祖仪式 。 李盖提还认为 “主格黎”这个词已经不见于现代蒙语 , 但满语中依然保存了这个词 。
“主格黎”到底是“祭天”还是“祭祖”呢?
罗新认为 , 祭天和祭祖 , 在内亚传统中也许是没有差别的 。 王恽《中堂事记》记载过 , 忽必烈举办祭天仪式时 , 就只有蒙元皇族能够参加 。 “上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 , 皇族之外 , 皆不得预礼也 。 ”
另一位匈牙利学者Lajos Bese则利用语言学研究和民族志成果指出 , “主格黎”这个词和仪式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西布里亚特蒙古语人群 , 他们至今仍然过着传统文化生活 。
1973年版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俄语词典》解释züxeli为:献祭动物之皮(带头和四蹄)放置在木杆上 。 Lajos Bese引用了鲍培的研究 , 指出“主格黎”仪式延续到当代 。 因此布里亚特人的züxeli仪式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蒙古秘史》里的“主格黎” 。
与蒙元同时代的西方旅行者 , 也记录了类似悬挂牲体祭祀的习俗 , 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 。

罗新:北魏“西郊祭天”是什么样的?// //
堂子图 , 出自《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但是 , 罗新提醒大家 , 虽然相关记载很多 ,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现代调查 , 去完全复原“主格黎”的历史原貌 。 因为同为阿尔泰人群 , 即使同为某一语族甚至更小亚文化圈的人群 , 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境 。 同源的宗教实践也会有众多细节变异 。 仪式更是如此 。
总的来说 , 在所有这些仪式中 , 牲体的全部或部分置于木杆上是普遍现象 。 类似“主格黎”的仪式在古代中国官方史书也屡见不鲜 。 《金史35·礼志八·拜天》:“金因辽旧俗 , 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 。 ……为架高五六尺 , 置盘其上 , 荐食物其中 , 聚宗族拜之 。 ”《辽史49·礼志·吉仪·祭山仪》:“设天神、地祗于木叶山 , 东乡:中立君树 , 前植群树 , 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 , 以为神门 。 ……杀牲 , 体割 , 悬之君树 。 太巫以酒酌牲 。 ”
然而 , 关于“木杆祭天”最丰富的内亚信息 , 被保存在满清的史料里 。 满清有“堂子祭天”的仪式 , 在文献中又被称作“设杆祭天”“立杆大祭” 。 从清代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一窥“堂子祭天” 。
福格在《听雨丛谈·卷五》描述了满人的祭祀 , “荐熟时 , 先刲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 , 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 , 献于神杆斗盘之内 。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堂子”一条 , 对“堂子祭天”仪式的详细描述:“国家起自辽、沈 , 有设竿祭天之礼 。 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室 , 名曰堂子 , 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 , 犹沿古礼也 。 既定鼎中原 , 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 , 建祭神殿于正中 , 即汇祀诸神祗者 。 ”
乾隆年间写成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 对“堂子祭天”有最为详细的描写 。 这本书把满清的祭祀分为三类:祭神(跳神)、祭天(还愿)、背灯祭 。 其中祭天的场所 , 就是堂子(tangse) 。
不同于北魏的“岁一祭” , 满清的“立杆大祭”一年两次 , 分别在春、秋举行 。 书中详细记载了如何准备祭祀用的松木杆 。 在祭天前一个月 , “派副管领一员 , 带领领催三人 , 披甲二十人” , 前往直隶延庆州 , 在“洁净山”中砍一棵松树带回 。 仪式所用的松树需要“长二丈 , 围径五寸” , 树上多余的树枝都要砍掉 , 只留下九节 , 这样“神杆”就做成了 。 一群人护送回来的“神杆”会用黄布包好 , 暂时安置在堂子南面的木架上 。 祭天前一天 , “神杆”才会被取出 , 插在堂子殿前中间的石头上 。
从北魏的“木主” , 到蒙元“主格黎”仪式的木杆 , 再到满清的“神杆” , 尽管仪式细节发生了变化 , 但木杆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 把祭祀的牲肉悬挂或者放置在木杆上 , 是内亚文化一个延续的传统 。
罗新进一步追问 , 是否存在更古老的共享文化 , 这种祭祀的内亚传统和中华传统有没有渊源?“以竿悬肉祭天”在古代中国也能找到对应物 , 那就是“碑” 。 根据郑玄对《礼仪》的注释 , 中国的石碑 , 最早的作用就是用来安放祭祀的肉 。
罗新对此的观点是 , 中华文化和内亚内化是可能有共享的地方 , 但这些共通之处未必是同源的 。 内亚文化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多样性;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 。
内亚的历史 , 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 把内亚文化 , 放到中国传统中去理解 , 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 如果仅仅遵循周、秦、汉、唐的传统 , 就会对内亚的传统视而不见 。 除了内亚传统 , 中国的长江流域、四川等地也有各自的传统 , 只有具备多元文化的视角 , 才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有所了解 。
- 别不信,最早把牡丹叫“国花”竟然是她!
- 本命年不顺利,要挂红“辟邪”,为何人们这么认为?
- 历史上诸葛亮究竟是否有过“七擒七纵孟获”?
- 秦朝那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鼠年说鼠(8)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
- 返京者深夜有家难回:“硬核防疫,以人为本”,为何这并不矛盾?
- 古代名画里的“女主角”,每个都是一段历史
- 河北的省级博物馆为何叫“河北博物院”,而不是“河北省博物馆”
- 历代皇帝为何自称“朕”?恍然大悟!
- 《出师表》成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上推崇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