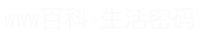一路“背”歌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一路“背”歌
| 一路“背”歌 |
| 历史深处的天全背夫 |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
一路“背”歌// // |
这是1903年法国人方苏雅拍摄的四川背夫从泸定背茶到康定的照片 。
新华社资料片
本报特约撰稿 聂作平
1911年,大清帝国宛如汪洋中的一条破船 。 这年夏天,帝国西部重镇成都,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的美国教师那爱德应清政府邀请,动身前往四川西部作一次为期数月的地质调查 。
那爱德既是地质学者,也是摄影家 。 沿途,他用黑白相机为后人定格了100多年前四川的山川形胜与风土人情 。 我注意到了其中的两张照片:崎岖的山道上,几个衣衫褴褛,弓着身子背负长条形重物的人,正在艰难行走 。 这些照片拍摄于闻名遐迩的茶马古道川藏段 。 镜头前的主角,就是曾经用肩膀扛起一条古老商道,尔后又渐渐消失于历史深处的天全背夫……
要有背夫,就有了背夫
最近15年间,我先后七八次前往雅安市天全县下辖的一座偏远小村庄 。
雅安以西,四川盆地开始向青藏高原过度,大地向着天空的方向缓慢而又固执地抬升 。 天全县城西距雅安市区约30公里 。 出天全县城往西,大约八九公里,就是我前往的小村庄 。 那里,两列青翠的山峰逶迄不绝,中间是潺潺流淌的青衣江支流天全河 。 小村庄位于其中一列山峰的半山腰 。 村外,两条小溪汇入天全河 。 因小溪时常干涸,故而得名大干溪、小干溪 。 顺理成章的,这座两条干溪旁的村子,也就得名干溪坡 。 后来,大概是为了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改干为甘,遂有了现在的名字:甘溪坡 。
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的小村庄,几排木结构的房屋依山就势,高高低低地拥挤在狭窄的台地上 。 一条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斗折蛇行,从村子中央钻过去 。 大约行走的人太少,铺路的石板角落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 。 雨后,苔藓如同青色的地毯,爬行着一只只肥大的蜗牛 。 白色的烟岚从对面的山巅飘过来,乘着一阵山风,又向远处飘过去 。 向西遥望,更为高大的山峰连绵如城郭 。 那里,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天险:二郎山 。 村头,一株碗口粗的杉树下,竖着一方两米多高的石碑 。 石碑上是苍劲的行书:古道背夫铭 。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就是为了这块碑 。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业已消失的群体:天全背夫 。
那一年,天全政府打算为背夫建一座纪念馆,并立一块碑 。 经朋友推荐,我受邀撰写碑文 。 一个初秋的下午,秋雨乍停,我来到甘溪坡,并采访了几位当年的老背夫 。 15年后,为了写这篇文章,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到了当年的采访笔记 。 只是,当我最近一次前往甘溪坡时,曾经采访过的几个老人只有一个还在人世,且已严重失聪 。 事实上,虽然做过背夫的天全人数以千计,如今还活在人世的,估计不到十个了 。 随着亲历者的不断凋零,这一古老的职业终将成为地方史料里几行了无生气的方块字 。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尤其是与西藏毗邻的四川和云南更是茶叶的主要产区 。 与这两个地区唇齿相依的西藏,虽然对茶叶十分渴求,却由于酷寒的高原气候,无法种植,只能依赖川滇茶叶入藏 。 在以马匹作主要动力的古代,内地主要为农区,不产马匹,西藏却盛产良马 。 这种出产的互补性使两个民族走到了一起 。 于是,茶马互市产生了,茶马古道也就呼之而出 。
据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茶叶是唐朝时传入西藏的 。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即今西藏)时,偶然在帐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常鲁公回答:“这是解渴去烦的好东西,名叫"茶" 。 ”赞普仔细察看了一下,笑着说:“我也有这种东西 。 ”并命手下人从库房中扛出一大堆 。 常鲁公一看,果然都是茶叶,而且品种繁多,分别有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出产的各种名品 。 从那以后,喝茶的习惯传入藏区 。 这种解渴去烦的东西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藏族人民来说,是十分相宜的 。 他们很快就将茶当作了生活必需品——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之类的记载 。 藏族民谚也有“汉家饭果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
茶马古道的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一条自普洱茶产地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迪庆、德钦,到达西藏芒康、昌都,然后再抵达波密和拉萨,尔后辐射至藏南的泽当和后藏的江孜、亚东,或者出境到印度和中亚;另一条由四川雅安一带出发,经天全、泸定、康定、巴塘到达昌都,尔后线路与滇藏线重合 。
不论是茶马古道的北线还是南线,大多数地区,运输茶叶的都是骡马,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 。 然而,茶马古道北线的天全到康定,这200多公里的路途,其间要翻越难以计数的大山,穿过多条冰冷刺骨的雪水融化的河流,不少路段只有一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且大多行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高大的骡马根本无法通行 。
有需要就有创造 。 无论帝王的意志还是大自然的严峻,都无法阻挡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愿望,更何况这样一条关系到两个民族、两个文化区域的重要商道 。 于是乎,天全背夫的出现成为必然,并因历时上千年的茶马古道而成为二郎山麓的一大“特产” 。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 这幅旧时茶馆里常常可见的对联,让川茶名扬天下 。 蒙顶山坐落在距天全只有50公里的地方,相传它的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 。 不仅蒙顶山产茶,蒙顶山周围百公里范围内的多个地区都以产茶著称 。
天全一带,自古就有种植茶叶的传统,遍布山间的茶园,已有上千年历史 。 地方史料记载,天全大规模种植茶叶,始于唐朝初年 。 其时,“天全东西河流为龙尾峡所阻,水道迫仄,潴为大泽,向有大小海子之称 。 ”一个后来被封为英烈侯的孟姓将军,凿开龙尾峡,从此水流通畅,水患平息 。 此后,他“于蒙山采茶子,于山谷间遍种之”“教其民以树艺采焙之法”,成为天全种茶之滥觞 。 载于《天全州志》的一首竹枝词,描写天全采茶的盛况说:“采茶刚趁月光明,大妇相随小妇行,采到春心尖纯处,春愁一缕发幽情 。 ”
藏汉接合部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包括天全在内的雅安地区生产的茶叶,绝大多数都用于边贸,人们称为边茶 。 始于盛唐的茶马互市让天全脱颖而出,天全茶叶声名鹊起;至于天全背夫,也在历史深处应运而生 。
拐子窝:仿佛用象形文字写就的史书
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甘溪坡采访时,70岁的李攀钰是几个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 那时,他身体精壮,穿着缀有补丁但洗得还算干净的衣服,大口大口地抽着叶子烟 。 他坐在一株挂满了红色果实的橘树下,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述逝去的背夫生活 。 15年后,我为了拍摄《中国影像方志》之《天全篇》而又一次看到他时,他已垂垂老矣 。 曾经挺直的背驼了,目光浑浊了 。 甚至,即便对着他听力仅存的耳朵大喊大叫,他也只能听得见零星的只言片语 。 至于比他更年长的几位老人,已经先后过世 。
在我和李攀钰的孙子交谈期间,大约是依稀听到了背夫两个字,老人原本昏暗的目光突然间亮了一下 。 之后,他长久地注视着门前的小路 。 ——距老人两三米外的堡坎下,古道曲折如蛇,穿过两排房屋后,扎进村后的林子 。 那就是昔年背夫们往返于天全与康定之间的必经之路 。
初到甘溪坡的人,都会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 那就是铺砌古道的青色石板上面,散布着一个个小小的坑窝 。 这些坑窝,人们称为拐子窝 。
拐子窝,和天全背夫人手必备的一件重要工具有关 。
甘溪坡村头的古道背夫陈列室,大约游客稀少,长期大门紧锁——至少,在它修成之后我去过的几次里,每一次都是铁将军把门 。 不过,透过门缝,依然能看到陈列在角落里的一种两三尺长的丁字形棍子 。 这就是背夫们终日捏在手中的拐棍,当地人把它称为拐子 。 这根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拐棍,是背夫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 可以说,没有它,背夫寸步难行 。
多年以来,生产好的边茶都用竹条包裹并扎成长条形,称为茶包子 。 每一个茶包子的重量是标准的:16斤 。 一般来说,一个背夫一次能背10到15个,最厉害的则能背重达320斤的20个乃至更多 。 茶包子一个接一个码到木制的背架上,背夫再将背架背负于双肩 。 路途上的每一天,从早晨出发到傍晚住下来,其间的十几个小时里,背架都不能从背上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再背上去极其麻烦,且沿途也很少有那么宽的地方可供解下又背上——因此只能一直背在背上 。
哪怕铁打的汉子,也不可能从早到晚不歇息,不吃饭,不小便 。 这时,拐棍就派上用场了:背夫需要停下来歇息时,只需用拐棍的一头撑住背架底部,便能将茶包子的重量转移到拐棍上,从而得以歇口气,喝口水或是撒泡尿 。
拐棍除了作为休息时的支撑,背夫还依靠它涉过险急的溪流,走过泥泞或积雪的山路 。 有时在山间遇到野狗或蛇虫,它又是自卫的武器 。 拐棍底部用坚硬的金属包卷,以延长使用寿命 。 意想不到的是,一代代背夫手持拐棍接力般地行走于途,在拐杖底部金属的一次次敲击下,古道上竟形成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坑 。 从天全到康定,无以计数的小坑仿佛是一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史书,忠实而深刻地记录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也记录了天全背夫的艰辛 。
李大爷的记忆
翻开15年前的采访本,我当年写下的采访手记依然清晰 。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有着淡淡秋日暖阳的下午,除了李攀钰外,其他几个老人中,还有另一个也姓李 。 他年事最高,做背夫时间也最长 。 因而,大多时候,都是他在回忆 。 可惜,当时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他李大爷 。
采访之前,我以为背夫是专职 。 李大爷明确告诉我,专职的背夫确实有,但非常少 。 他们绝大多数本身都是种地的农民,每到农闲,趁地里农活少,出来兼职做背夫,以便挣一笔庄稼之外的额外收入 。 想想也是,天全地处山区,满目青山,耕地少而珍重 。 如果只从土里扒食,压根儿就养不活一家人 。 幸好,只要身强力壮,只要吃苦耐劳,还可以当背夫 。 以甘溪坡为例,当时村里的男人,只要是能动弹的,几乎都做过背夫 。
李大爷记忆中,天还没亮,他就在家里急忙吃完早饭,走到十多里外的天全城,从商号取了茶包子往回赶 。 一直要走到满山暮色,才又回到甘溪坡 。 家中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背着沉重的茶包子,向西边天际更高更陡的大山缓缓前行 。 从天全到康定,如果背得轻的话——所谓轻,一般指背10个以下的茶包子;来回一趟需要11到12天 。 如果背得重的话——所谓重,一般指背10个以上的茶包子——李大爷自豪地说,他的最高纪录是20包半——来回一趟则需要15天 。
去时负重,回时也不会闲着 。 从天全到康定,背夫背上是茶叶;从康定回天全,背夫背上换成了羊毛 。 今天,天全到康定已通高速,100多公里的路途,不过几十分钟行程 。 但在高速通车之前,即便已经有了川藏公路,由于要翻越二郎山,大部分路段崖陡坡险,汽车也需要好几个小时 。 更何况,在既没有汽车也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的年代,背夫们必须背负两三百斤的茶包子,一会儿穿行于原始森林,一会儿涉过冰冷湍急的小溪,一会儿攀上白雪飞舞的二郎山垭口,一会儿贴着崖壁小心地从两尺宽的石埂上越过万丈深渊……尤其天全多雨,一年有200多个雨天,其行路之难,就像天全民间俗话所说的那样:“天天下雨天天溜,没有鞋爪子钉钉,上不了梅子坡顶顶 。 ”——梅子坡只是县城附近一座低矮小山,其行走已是如此艰难,何况横亘在盆地与高原之间那些三四千米的大山 。 所以,当年的行走极为狼狈,当地人称为“上山学牛叫,下山做狗爬 。 ”种种艰难与危险,哪怕几十年以后再追忆,我也能感受到几个老人的沉重和辛酸 。
背夫们背上除了茶包子,还有沿途要吃的粮食 。 从天全到康定,虽说大山纵横交错,但就像藏在林间的甘溪坡一样,每隔上十多里路途,就会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或集镇 。 不论村庄还是集镇,一定会有供来往背夫歇脚的驿站——当地人把这种最低档的既卖简单食品又提供住宿的驿站称为幺店子 。 川话里,幺,也就是小的意思 。 像甘溪坡,它是茶马古道出了天全后的第一座村庄,当年便有好几家生意兴隆的幺店子,并有茶马古道第一站的美称 。
脚基坪、紫石关、小渔溪、长河坝、两路口、鱼通沟……哪怕背夫生涯业已结束几十年,李大爷对那些曾经熟悉的驿站依旧如数家珍 。 幺店子都提供饮食,但出于节约的天性,背夫们都是自带玉米面和玉米饼,以及盛水的葫芦 。 白天忙着赶路,累了饿了,伸出拐棍将背架一撑,吃两个冷玉米饼,喝几口冷水就算午餐 。 如果能靠着大树或岩石打个盹,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 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幺店子门前的青布帘招,艰难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又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 。 于是,在老板娘的招呼下,背夫们次第放下背架,走进院子,一个接一个地借用幺店子的锅灶,拿出自带的玉米面,煎几个玉米饼,熬半锅玉米羹 。 按惯例,幺店子都会出售豆腐 。 对住宿的背夫,一律赠送豆腐一块 。 许多年过去了,李大爷还记得鱼通口那家幺店子,“那家的老板娘姓啥我忘了,只记得脸上有麻子,手脚麻利,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每个背夫都送一块 。 晚饭就是玉米饼、玉米羹和烧豆腐,胀得肚皮痛,还想吃 。 ”
这种幺店子收费低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块钱左右,当然也极为简陋 。 甚至,就连床也没有,全是地铺 。 偌大一间屋子,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是一张和屋子同样大小的席子,席子上是一床和屋子同样大小的被盖 。 至于枕头,是从山上砍来的一根脸盆粗的大树,从中剖开,便成为一个两丈长的横跨一间屋子的巨型枕头 。 这样的“床”,能睡下二三十个人 。 晚上,背夫们吃过简单的晚餐,迫不及待地倒下睡觉 。 虽然跳蚤与臭虫成群,汗臭与脚臭弥漫,但疲惫是最好的安眠药 。 片刻之间,屋子里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打鼾声、磨牙声 。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从幺店子背后的深山老林里,偶尔传来的猫头鹰凄苦的夜啼……
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
李大爷一家几代人都做过背夫 。 在我的采访笔记里,记录了他讲的关于背夫的两个故事 。
故事之一是甘溪坡附近某山村,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猪 。 猪养肥了,打算弄到山下城里去卖 。 路又陡又窄,没法像山下那样把猪装进用竹条编成的猪篓再抬进城 。 无奈,只得请了力气最大的一个背夫,把猪背下去 。 谁知,活着的猪不比茶包子,不断在竹篓里挣扎 。 要命的是,当背夫小心地贴着石壁经过一道高高的悬崖时,猪的挣扎终于让背夫失去平衡,连人带猪跌了下去 。 等人们从远处绕到山沟时,人和猪都已气绝身亡,唯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在弥漫 。 为了赔偿背夫,养猪的这户人家只好变卖了祖传的两亩地 。
故事之二的主角是李大爷的父亲 。 民国二十五年,即公元1936年,国民政府开始修筑从天全到康定的公路 。 这段历史,我曾见过摄影家孙明经当年拍的照片 。 他的镜头前是一群正在赶路的背夫,背夫脚下,不是逼仄的山路,而是宽阔平整的刚完成的毛坯公路 。 至于背夫所背的东西,也不是茶包子,而是供筑路工人食用的大米 。 孙明经为这幅照片题写的说明文字是:“天全川康公路之背米者 。 过飞仙关而至天全,再向西南行,在二郎山一带,公路蜿蜒于群山之上,高2900米,森林密布,人烟绝迹,工程艰巨,路工所食之米,需自雅安等地背负数日之行程,前往施工地带接济 。 现公路已修通至泸定,与旧道相汇合 。 ”
孙明经可能不知道的是,筑路期间,天全背夫除了背米,还背过死人 。 据李大爷讲,由于工具太原始,环境太恶劣,筑路工人不得不腰系长绳,悬在半空作业 。 为此,工地上每天都有人遇难 。 这些遇难者的尸体,绑在一块木板上,背夫把木板连同尸体一起背到天全 。 根据路的远近,有时要背两天,有时要背三天 。 因为背的是尸体,幺店子自然不同意入住,背夫们只能露宿于凸出的山崖脚下 。 夜里,凄风苦雨,四周一片昏黑,近在咫尺的林子里,传来野兽的哀鸣 。 眼前除了一堆微弱的篝火,只有一具渐渐发臭的尸体……
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
按我最初的想象,背夫这种以命相搏的职业,只能属于男人,且只能属于精壮的年轻男人 。 然而,采访中却得知,行走在天全到康定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男人,竟然还有女人 。 与男背夫相比,女背夫更加艰难和憋屈 。
天全山间多竹,每到三月,春笋竞发 。 其时,家有女背夫的人家就会钻进竹林,捡一些笋壳回家 。 就像背夫离不开拐棍一样,女背夫还得多一样装备,那就是笋壳 。 小心擦去笋壳上的绒毛后,再用剪刀略作修整,使其两端卷起,呈一个凹槽形 。 女背夫领取茶包子上路之前,一定会记得带上几片笋壳 。
原来,背夫从早晨出发到晚上住店,其间,背架不能从背上取下来 。 男背夫小解时,只需用拐棍撑住背架即可 。 性别不同,女背夫没法像男背夫那样 。 女背夫只能将笋壳贴近私处,让尿液顺着笋壳的凹槽流到地上,以免打湿裤子 。
天全地处民族交界处,自古多匪 。 虽说背夫们总是十个八个结伴而行,也未免有赶不上队伍而落单的 。 尤其是女背夫,常常沦为匪徒抢劫甚至凌辱的对象 。 至于一间房子就是一张超级大床的幺店子,女背夫也只能放下尊严,和那些陌生男人挤在同一床被盖下 。 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草根来说,所谓尊严,远不如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几块散碎银两更重要、更实在……
那么,如此含辛茹苦地背一趟,到底能挣多少钱呢?李大爷的说法是,就普通背夫来说,如果背十来个茶包子的话,大概能挣5块大洋 。 其时,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 。 放到今天,也就四五百块钱的样子 。 十多天辛劳,只有四五百块钱收入,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 但彼时彼境,100多斤大米,却是一家人赖以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和支撑 。 对这些卑微的生命来说,活着,哪怕艰难地活着,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
苍茫茫的天涯路
蜜蜂采蜜,没想到采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春天;为了生计而奔走的背夫,他们一定也没想到,一代接一代的行走,支撑起了一条古老而繁荣的商道 。 从某种意义上讲,藏汉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正是通过一双双布满老茧的肩膀和双脚来完成的 。
前面说过,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 。 对唐朝来说,除了想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 。 也就是以茶治边 。 因此,历代中央王朝对茶马互市的政策,时时都在调整 。 总体来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由国家专营,一种是公私皆可经营 。 唐朝末年,朝廷下令所有种茶户必须把茶树全部移植到官方茶场,茶叶产销全由政府垄断 。 北宋初年,又改由专门的茶户种茶并焙茶,政府专款收购后再经营 。 北宋末年,开始实行茶引法,也就是商人可以经营边茶,但要向政府交钱取得茶引——相当于今天的配额 。 明朝初年,为了执行羁縻政策,朝廷对茶叶严加管制,茶引制改为引岸制,即由国家固定产销地区及课税标准 。 鉴于天全的重要性,朝廷在天全县城设置了茶马司和茶局,负责茶引批验 。 调运茶叶的工作,全部交给军队,以至于“十里为铺,铺有兵,兵有程,月有给,苟不如式,罪罚随之 。 ”为了杜绝民间私贩茶叶,法令竟严酷到“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凌迟处死”的地步 。 至于茶树苗和茶籽,更是严禁运出藏汉交界的飞越岭和马鞍山 。 直到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间,朝廷对茶叶的严管终于不再,政府开始允许私人经营,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
是故,从15世纪末年的弘治年间起,以茶叶为大宗的边贸给天全带来了一个富庶锦绣的花样年华 。
天全下属的始阳镇,是仅次于县城的第二大镇,也是曾经的边茶集散地之一 。 如今,始阳镇略显杂乱的房舍之间,鹤立鸡群地残存着一片老建筑 。 这片老建筑虽然破败,却依然以高大的梁柱和精巧的结构、庞大的体积透露出曾经的宏伟 。 这就是世代经商的高氏家族筹巨资于清朝初年修建的茶叶仓库 。 据考证,它也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仓库 。 清朝中期,由于经营不善,高氏家道中落,仓库被朝廷收购 。 如今,它已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残存的面积仍超过两千平方米 。
一张附录于清代《天全州志》中的始阳地图则显示,就在这片弹丸之地上,曾经修建有众多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贵州会馆——会馆,是同一籍贯的商人们敦叙乡情,沟通有无的会所 。 此外,还有武庙、奎阁、文昌官和书院等一系列公共建筑 。 几十年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在川西考察期间来到天全,事后撰文称赞始阳镇说:“庙宇甚多,建筑均颇宏丽,商贾以茶叶和布匹销售为主 。 ”
如果说这些繁荣是台前的话,那么在台后为繁荣默默效力的,就是籍籍无名的背夫 。 没有他们的艰难行走,就没有这些繁荣昌盛 。
救命树和暗号树
深入天全考察之前,我一直以为,从天全通往康定的茶马古道只有一条,也就是李大爷他们所走的那条 。 随着考察深入和查阅地方文献才得知,事实上,背夫们接力于途的古道有两条 。 一条,就是从天全向西经甘溪坡而行,即李大爷和甘溪坡背夫们世世代代走的这一条 。 这一条沿途多是高山峡谷,道路狭窄危险,因而称为小路 。 小路又有新路和旧路之分 。 旧路通行于唐朝到明初;新路通行于明初至上世纪40年代 。 无论旧路还是新路,都需要翻越险峻的马鞍山和二郎山——李大爷对当年经行的马鞍山记忆犹新 。 他说,由于地势高峻,每年九、十月山中就大雪纷飞 。 有时候,雪把路完全盖住了,只能用拐棍把雪推开,才能隐约看到路基 。
与小路相对的是大路 。 大路又称始阳路 。 从雅安或名山而来的茶叶,西行进入天全境内的多功坝后,溯荥经河上行,翻过飞越岭,经汉源后抵达泸定,进一步到达康定 。 大路初辟于隋朝,唐朝以降,历代都有修整和拓宽,相当于政府养护的官道 。 与小路相比,大路更安全也更好走 。 不过由于绕道,所耗时日更多 。 对许多背夫——尤其是家住小路旁边的甘溪坡一带的背夫来说,他们的首选仍是更加危险的小路 。
匪徒拦劫,野兽出没,道路崎岖,山洪和泥石流迅雷不及掩耳,背夫生涯危机重重 。 作为天全末代背夫,李大爷曾遭遇过多次危险 。 一次是在长河坝遇到抢劫的土匪,幸好腿脚灵活,跑得快,趁着土匪抓住他之前扔下背架跑进了茂密的林子——对沉重的茶包子,土匪没有兴趣 。 另一次是在门坎山遇到山洪 。 即将跌进山谷之际,山崖上的一株栎树挡住了他 。 “要不是那棵栎树,哪里还有人哦,又哪里还有我这满堂儿孙哦 。 ”几十年过去了,李大爷对那株有救命之恩的栎树饱含感激 。
经由天全作家李存刚指引,我们一行沿着简陋的石板路穿过甘溪坡 。 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如同几十年前那些趁着农闲去做背夫的先辈们一样 。 尽管退耕还林后,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要想手头有几个钱,要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些,还是得出外打工 。 偶尔能看到三两个老人和妇女,面容沉静 。 当然,还有留守在家的儿童 。 他们清脆的笑闹声与村后树林里传出的画眉声交织在一起,让这个沉寂的小山村多少有了一些人间烟火的温暖和柔情 。
走到村子最西边 , 一栋废弃了大半边的木屋旁 , 有一块小小的台地 。 台地上 , 杂草过人 , 草下横卧着一株树 。 树早枯死 , 没有树叶 , 甚至也没有枝桠 , 只余下光秃秃的树干 , 叫人无法分辩它到底是一株什么树 。 走近细看 , 树身上有许多用刀刻下的痕迹 。
李存刚告诉我 , 背夫时代 , 背夫们从天全县城或是始阳镇领到茶包子后 , 家人一般都会送到甘溪坡 。 在这里 , 家人依依惜别 , 看着背夫佝偻的身子 , 慢慢被远处的林子和山峰吞没 。 由于路途遥远 , 沿途又杀机四伏 , 背夫的行程常有不测 。 为此 , 背夫与家人分别前 , 就在路旁的这株大树上 , 用刀刻下一个记号 , 并约定返程日期 。
到了约定日子 , 家人见背夫没回来 , 就到树前去察看 。 如果发现当初刻下的记号被削去 , 就表明背夫已经从康定安全回来 , 并到天全或始阳去排班 , 准备下一趟行程了 。 如果记号还在 , 那多半凶多吉少——背夫还没有回来 , 他们要么因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耽搁在路上 , 要么作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大约就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画与削平 , 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终于干枯并倒下 , 成为茶马古道上一处令人扼腕的冷风景 。 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 真实地唱出了背夫家人对远行者的期盼与担忧:“阳雀叫唤口朝天 , 小妹望郎一天天 。 白天黑夜望郎归 , 迟迟不见郎回转 。 ”
古道背夫铭
天全多山 , 县城却幸运地据有一片两山之间的坝子 。 所谓坝子 , 乃是川话里对小型平原的称谓 。 坝子西缘 , 两山越靠越近 , 湍急的天全河就从两山缝隙里潺湲而过 。 这里 , 古称碉门 , 盖因两侧山峰对峙如门 , 是进入藏区的咽喉要道 。 到了清朝 , 政府在这里修筑关楼 , 管理进出商贾 , 故又称为禁门关 。 如今 , 不论碉门还是禁门关 , 都是天全县城的代名词 。
距早就荡然无存的禁门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 有一家开设在一栋极为简陋的老房子里的小吃店 。 小吃店没有店招 , 因旁边是川藏公路上的一座大桥 , 人们便把它称为桥头堡 。 这是一家十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网红店 , 店里出售的食物只有两种:鸡肉抄手和麻辣鸡块 。
“出了禁门关 , 性命交给天” , 这是几十年前天全背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 作为进入藏区之前的最后一站 , 出了禁门关 , 意味着从盆地进入高原 , 意味着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 , 意味着不动声色的高原和林莽里充满令人窒息的杀机 。 只有当背夫们顺利地把茶叶背到康定 , 再背着康定的羊毛顺着古道一步步走下高原进入盆地 , 遥遥地望见对峙如门的碉门时 , 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才会油然而生 。 于是 , 哪怕最贫困最节俭的背夫 , 也忍不住要到路边店里买一碗酒喝 。
这种潜移默化的风俗 , 慢慢演变为后来许多自驾或是骑行入藏者的仪式:进藏前 , 在天全作最后的休整与补给 , 其间一定要到桥头堡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抄手 。 如是 , 一种壮行的感觉油然而生 。 出藏后 , 同样的鸡汤抄手又有了凯旋接风的意思 。
15年前 , 我和两个朋友坐在桥头堡吱吱呀呀的木楼上 。 楼下 , 几十只刚从乡下收来的土鸡不时在笼子里发出傲慢的长鸣 。 我们就着麻辣鸡块和鸡汤抄手 , 痛饮当地出产的猕猴桃酒 。 酒后 , 我开始为渐行渐远的天全背夫撰写那篇后来勒石于甘溪坡的《古道背夫铭》 。
如今 , 西康高速已经通车 , 天全就位于高速路旁;正在修筑的川藏铁路 , 也将在天全设站 。 曾经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甘溪坡 , 远离了高速和铁路 , 孤零零地掩埋在一片翠绿的林子里 。 只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 , 或许还会专程绕道而来 。 他们顺着陡峭的山路盘旋而上 , 走进村庄 , 观看一番 , 感慨一番 , 尔后离去 。
高大的石碑下 , 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已然落幕 。 甚至 , 正在被遗忘 。
然而 , 正如我在撰写碑文时认定的那样 , 那群面目模糊 , 没有留下姓名的背夫 , 我们有理由铭记他们 , 纵然他们已经随着那条古老的商道消失在历史深处……
- 别不信,最早把牡丹叫“国花”竟然是她!
- 本命年不顺利,要挂红“辟邪”,为何人们这么认为?
- 历史上诸葛亮究竟是否有过“七擒七纵孟获”?
- 秦朝那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鼠年说鼠(8)
- 中国最“富”两大隐形家族,后代沉寂多年,如今改变了大半中国
- 返京者深夜有家难回:“硬核防疫,以人为本”,为何这并不矛盾?
- 古代名画里的“女主角”,每个都是一段历史
- 河北的省级博物馆为何叫“河北博物院”,而不是“河北省博物馆”
- 历代皇帝为何自称“朕”?恍然大悟!
- 《出师表》成为千古“至文”,历来为忠良义上推崇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