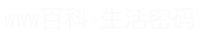讲座︱刘士永:抗战时期的军事营养学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讲座︱刘士永:抗战时期的军事营养学
“营养”一词在现代被定义为一种有机体摄取和利用食物养料的生物学过程 , 但在过去 , 这一概念往往与传统食补或膏粱厚味的庶民饮食观念等同 。 这一转变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发生的?西方式的营养学理论是如何在中国建立与发展的?现代中国人的营养标准又是如何确立的呢?
2019年11月12日 ,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刘士永受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行题为《抗战时期军事营养学浅释》的学术讲座 。 本次讲座由孙竞昊教授主持 ,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以及华东师大的多位师生参与了讲座 。 刘教授是著名的医疗史、环境史研究学者 , 此次讲座所报告的是他的最新研究内容 , 即探讨抗战前后中国营养学建立、变迁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
军事营养学研究的缘起与理论来源
在论述台湾1949年之后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学知识时 , 学术界存在一个著名的“Y线理论” , 其主要内容是将1949年前大陆的医学经验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经验合流 , 简单地交织成1949年后台湾医学发展的基础 。 但刘士永教授指出 , 这样一个粗略的理论在应用于营养学、生化学这些新学问时 , 便暴露出诸多不足 。 他发现台湾的营养学理论中几乎难以见到日本殖民医学的影响 , 其所继承的都是大陆单方的经验 , 而这些经验也不是全面的 , 往往是来自特定地区或人群的片面经验 。 这些现象表明 , 要探寻当代台湾营养学理论的缘起 , 便不得不追溯1949年前的中国大陆营养学的发展历史 。
刘教授介绍道 , 他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前营养学学会会长Kenneth J. Carpenter关于现代营养学分歧的理论 。 Carpenter认为 , 美国营养学和欧陆营养学之间存在关注点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欧陆营养学以消化生理学为基础 , 重视热量、蛋白质以及人体对于这些成分摄取和吸收 。 但是 , 营养学在19世纪后期进入美国之后发生很大的转折 。 20世纪初 , 美国生物学、化学学者对食物中的营养素展开研究 , 他们工作的重点从食物的消化吸收转化为食物中维生素、矿物质、脂肪等具体营养素的分类及其对应的疾病现象 , 生化学的分析取代消化生理学成为美国营养学的基础 。
战后台湾的营养学体系同時关注营养素与烹调方法 , 换言之 , 其所重视的是如何保存食物中的营养素 , 这与重视消化生理学的日本殖民医学截然不同 。 既然不来自日本殖民医学的经验 , 那么台湾的营养学知识究竟从何而来 , 又为什么在1950年代会突然出现所谓的富强米实验?这些都构成了刘教授研究的问题基点 。 其实所谓“富强米” , 是一种富含多种维生素的混合米 , 其主要的宣传口号是吃一碗米就足够一人一天的营养量 。 由此引出的是最低营养摄取标准和最低维生营养量两个概念 。 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但在台湾的报告中 , 二者不加区分、混合的情况十分严重 。 所有这些战后的台湾营养学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来自台湾本土 , 那么它究竟移植自哪里?
刘教授讲座进行中
战前中国营养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在介绍完报告的选题缘起和理论依据之后 , 刘教授正式开始探讨1949年前中国营养学的发展历史 。 中国的营养学的起点 , 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代齐鲁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营养学研究 。 前者主要受到德式医学、消化生理学的影响;而后者在耶鲁大学教授Russell Chittenden的支持之下 , 从生理学系分离出独立的生化学系 , 营养学研究也开始进入到膳食营养素的定量分析调查领域 ,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出现以生化学为基础的美式营养学研究 。
这类新式营养学机构在战前进行了上海工人与童工膳食的一系列调查研究 。 不难发现 , 从调查区域和调查对象来看 , 这些研究真正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保证童工成为正式工人时 , 不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单位劳动力的下降 。 这类报告混杂了国家对工业化、都市化的期待 , 而这正是欧陆营养学自创立以来就包含的关怀 , 但特殊的是 , 中国的这些报告所采用的调查方式是具有美国生化学特性的营养素分析 。 1938-1939年 , 由北京协和医院生化学系主任吴宪为首 , 提出《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的报告 。 该报告的目的 , 是希望能够作为国民政府卫生部提升营养摄取量的一个基准 。 但从报告内容本身来看 , 这份报告关注的是如何为国家富强提供强壮的工人 , 而且它取样的对象是作为特例而非常态化的上海以及上海已经被工业化的工人 。 它忽略了对广大内地的膳食了解和近九成的农村人口 , 而事实上 , 这部分群体的膳食才是当时中国营养学真正应该调查和发展的重点之一 。
这一系列报告都包含着近代中国社会对于工业化的殷殷期待 , 即以营养增加改善民族体质 , 达到富国健民或者是强兵的目的 。 另一方面 , 这些报告也透露出一个与抗战开始之后截然不同观点: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瘦弱 , 正是长期营养不良下的结果 。 与之相应的期望正是 , 中国在达到西方的营养标准之后 , 又何尝不能有西方一样高大健硕的身体?营养学要顾及的不仅是民族之健康 , 甚至是未来中国人应有之体魄 。
讲座现场
抗战时期的营养学发展
但是 , 抗战开始之后 , 营养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为工业经济提供健康工人的问题 , 还包括为逃难人民提供基本营养所需的问题 。 1937年在上海即已成立难童营养援助委员会 , 如何用有限的捐助支撑难童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 , 是援助委员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 此时的难童已不再是工业经济的预备队 , 只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饥民 , 于是针对他们的营养标准遂转变为:保证他们不会因营养不良而生病或死亡 。 在1930年代的上海 , “营养”这一概念在时人眼中和食补、高粱厚味等庶民饮食观念相仿 。 但在抗战开始之后 , 营养学开始被认为是一门西方医学的专业 , 营养学知识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加以推广 。 在西南大后方 , 西方“食物即能量”的概念被灌输到民众之中 , 社会福利救济与 “营养”、“健康”等要素逐渐结合 。
就当时军事医学和抗战救护情况而言 , 美援机构在重庆重新整合 , 以美国医药援华会为主 , 成立美国联合救济总署 。 战前在上海从事营养调查的知识分子也向西南大后方移动 , 担任军医 。 同时 , 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中央军医学校等新式军医机构 , 以及陆军营养研究所、中央卫生实验处营养组等战时营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 其中 , 陆军营养研究所专门针对士兵平时及战斗时期营养的配比和调配研究 。
这些机构的士兵营养调查显示 , 当时士兵的营养情况十分糟糕 。 根据1938年的一项调查 , 中国江西部队膳食所含的热量仅2469卡 , 同时的美英国士兵有3800多卡 , 日本士兵也达2980卡 。 而1942年内陆战区营养与热量调查显示 , 前线作战的士兵的热量摄取甚至比1927年前后平民的情况还要低 。 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如何保证士兵的作战任务 , 是当时军医主要关注的问题 。 同一时期的日本营养学并没有出现生化学完全取代消化生理学的趋势 , 相比于营养素分析 , 日本营养学更重视膳食调查 , 其进步基本表现在研发各种消化酵素、提倡膳食均衡等方面 。 因此 , 战争时期日本的兵食也体现出重视食物营养的供给与消化的特征 。
“中国体质论”的提出
根据美方军医Water S. Jones的报告 , 可以看到二战期间对美国对中国的医药援助极为多元 。 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医疗器材设备 , 对军医与救护兵的训练 , 乃至于直接把美国战场救护单位送上前线与中国军人并肩作战 。 但是 , Jones也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军队没有正确的营养膳食观念 , 缺少军粮补给计划 , 而他批评最多的是中国军人大量上报自身存在脚气病、下肢水肿、夜盲症等问题 。 Jones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士兵没有按规定吃完美军提供的K口粮 , 并对这一情况极为愤怒 。 但是 , 等到滇缅部队中的英军、印度士兵也报告了相似的问题之后 , 美方军医开始重新审视中方士兵对美军配给的军粮抱怨 。 1942年初 , 中方在美方顾问建议下 , 针对滇缅远征军实施“中国军队营养之研究” 。 这项研究发现 , K口粮所含的营养素实际上无法被中国士兵充分吸收 。
K口粮
在这一背景下 , 以万昕为首的陆军营养研究所得以成立 , 并进行中国军人体质、营养素等方面的相关调查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调查的项目中杂糅了欧陆的消化生理学和美国生化学的内容 。 抗战时期 , 消化生理学和生化学逐渐融合的情形在中国十分显著 , 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在英国、日本出现 , 甚至在美国也很少见 。 这一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 一是中国军队究竟需要哪些营养素 , 一是中国军人的体质能否吸收等问题 。 部分中方军医指出 , 中国人所需要的营养标准与西方人不同 , 但美方军医一开始十分抗拒这一观点 , 甚至嘲讽地称这是“带有中国哲学意涵的医学想象” 。 1944年由陆军营养研究所主持的一项中国士兵糖化血红蛋白的调查 , 发现中国士兵的血红蛋白偏低 , 但是它的单位带氧承载量较高 , 这表明中国士兵不需要太多的动物蛋白质 。 这引出的论断是 , 中国人需要的营养的总量和比例搭配与西方人存在差异 。 在此基础之上 , 中国体质论的观点达到高潮 。 譬如 , 周凤镜在《目前与今后我国国民营养问题之研讨》提出 , 中国人的体质与经济可能正符合战争时期的现实需要 , 能在经济与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 。
在上述中国营养学发展的过程中 ,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变化 。 1938-1939年的中国人最适营养量报告 , 透露出的是以营养学改善国民体质 , 以健康的工人推动经济的工业化的期望 。 这是一个富国强种的过程 。 但抗战时期营养与体质的研究却显示出另一条路线:中国士兵能在战时紧张的经济供应和困顿的内外情形之下 , 还能保持较高的战斗能力 , 正是因为中国人经过数千年的演化 , 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量 , 也对一些营养成分没有那么强的吸收能力 , 却仍能绵延民族数千年的关键 。 中国军事营养学论述遂以“最适量标准” , 替换战前重视之“西方最佳标准” 。
在报告的最后 , 刘士永教授还提到军事营养学在战后台湾的一段小故事 。 上述这套战时发展出来的中国营养学研究在国共内战时期遭受较大挫折 , 当时的营养学家也四方流散 。 我们因此对战时营养调查研究站的具体运作情况始种不得而知 , 仅能从1960年代台湾嘉义水林乡的“小白宫”营养工作站历史中瞥见一角 。 小白宫当时承担的营养研究任务 , 造成了当时乡民间谣传美国在台湾打造超级士兵 , 以便投入越南的战事当中 。 刘教授总结道 , 世界各地的军事营养学的发展从未脱离过这类想象 , 只是中国营养学有一特别的插曲 , 即在打造强壮士兵的目的之外 , 还嫁接了中国人体质这一概念 。 如果没有这一概念 , 乳糖不耐症不会被注意到 , 中国人对植物蛋白的吸收度大于动物蛋白的现象 , 也不会那么早被发现 。
在之后的提问环节 , 在座师生就“营养学与’东亚病夫’等形象的塑造”、“营养学与人种体质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切的讨论 , 刘士永教授也一一作出详细的解答 。 讲座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 合纵连横︱魏安僖王继位之初联弱抗强的尝试
- 国博讲堂︱孔祥星:“破镜重圆”的习俗是何时出现的?
- 讲座︱杨天宏: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的军阀形象
- 陈晓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开创者主持的风满楼丛书
- 周运︱钱穆、顾颉刚赏识的学者黄少荃
- 访谈︱陈默:蒋介石也知道要“论持久战”,但时常南辕北辙
- 】档案春秋︱阿部规秀之死详探
- 高山杉︱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
- 栾保群《梦忆》拾屑︱海东青、千里独行
- 讲座︱赵庆云: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档案与旧人摭忆